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n China——Based on the Arbitration Right of Athletes in CAS Arbitration System
-
摘要: 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运动员等提供了包括仲裁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服务,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裁决难以达致程序和实体正义。作为法律服务体育的重要领域,CAS的仲裁体系极大损害了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的仲裁权益。我国未来体育仲裁体系构建应以维护体育比赛的持续性、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利、追求程序和实体正义为目标,保证仲裁组织结构设计合理,均衡司法渗透,遵从当事人意愿、兼顾效率,尊重合理期待和保障当事人充分参审权,助推仲裁程序和仲裁结果达致"接近正义",推动"依法治体"有序发展。Abstract: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in Lausanne provide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tria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and individual athletes, etc.; but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eems difficult in reaching th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Therefore, the arbitration system in CAS has greatly damage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thletes.The Chinese arbi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sports competitions, protecting the legal rights of athletes as well as the pursuit of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as the goals.The system design should ensure the rational design of the arbitra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 balance of the judicial infiltration.And it should also comply with the wills of the parties, take into the account of efficiency, respect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nd ensure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trial.It then will boost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s and results to achieve "access to justice" and promote the "governing sports by law" as well as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
随着商业运作被引入体育领域, 体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 全球体育产业产值占全球GDP的2.0%, 韩国更是达到了3.0%[1], 体育产业在欧美国家都是排名前10位的重要产业之一。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产出(总规模)为1.7万亿元, 2015年较2014年增长了26.02%, 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0.64%增长至0.80%[2]。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现代体育运动的娱乐性、商业性趋向, 并呈现专业化、商业化、全球化的特点。当资源有限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时, 2个或多个主体之间追求资源或利益时难免发生冲突和纠纷, 亟待建立有效的社会机制控制、削减冲突与纠纷, 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作为社会活动的体育运动在迅猛发展的同时, 体育纠纷在数量上呈现爆炸式增长。“随着金钱和财富在体育领域内的流动, 赢得比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所谓‘重在参与'的说法已经一去不返。运动员们开始服用各式各样可以提高比赛成绩的药物, 为了赢得比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对优秀运动员而言, 赢得比赛就赢得了金钱和财富”[3]。多元化的纠纷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新要求, 当内部救济业已用完, 作为一种带有民间性质的纠纷解决机制, 仲裁具有专业性、保密性、灵活性、时效性、低成本等天然优势。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催生了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的产生, 在一系列处理国际体育纠纷的仲裁机构中, 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CAS)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
1. CAS仲裁体系概述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CAS成立于1984年,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CAS从最开始的一案难办到现在每年受理500件以上体育纠纷案件; 从几乎完全受控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NOC)等有关机构到现在被广泛认为是解决体育纠纷的最高仲裁机构。CAS的广泛仲裁权受益于全球民商事仲裁的成熟发展, 签署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国家也就承认和执行CAS做出的仲裁裁决。截至2017年1月8日, 《纽约公约》已有156个缔约国, 加之IOC、NOC的积极推广和强制性仲裁协议的签订, CAS仲裁权得到所有单项奥林匹克体育项目联合会、众多非奥林匹克体育项目联合会的认可, CAS裁决书因此有了类似于既判力的保障。
1.1 CAS的成立及其发展历程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独立机构有能力就国际体育纠纷做出权威性、约束性、可执行性的裁决。体育运动时效性、专业性、突发性等特性决定其无法总是依靠国家司法系统解决争端, 毕竟诉讼程序显现的周期长、成本高、对抗性强等弊端, 并非体育纠纷的最好解决方式。全球化的实然结果是体育全球化, 体育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即纠纷国际化, 纠纷国际化的应然结果便是纠纷解决机制全球化。建立一个能在全球范围内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专业、方便、灵活和廉价的纠纷解决服务机构已成为必要。1981年当选为IOC主席的西班牙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充分认识到建立全球性体育仲裁法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2年, IOC在罗马举行会议, 决定由前国际正义法庭副主席、塞内加尔籍法官凯巴·姆巴伊带领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的相关规则。1983年4月6日,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8次会议批准成立CAS。CAS首任主席便是凯巴·姆巴伊。
CAS的口号是“公正、快速、免费”, 其使命是为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纠纷提供中立性、权威性的解决方案, 工作内容包括对当事人提交的纠纷提供普通终裁, 对已在体育组织内部进行过裁定的纠纷予以上诉仲裁, 同时也提供不具有约束力的、与体育相关的咨询意见。CAS成立之初共有60名仲裁员, IOC、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和NOC各推选15人, 最后15人由上述已确定的仲裁员提名确定。众所周知, 大多数体育纠纷的争议双方是运动员和IOC、IFs、NOC等, 但CAS仲裁员却均由IOC、IFs、NOC直接选出或与其存在重大利害关系, CAS主席由IOC主席任命, IOC负责CAS的行政管理同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如此极端化的“一边倒”运作模式自然难以保证CAS的中立性、独立性, 进而影响其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很快, 明显缺乏独立性的CAS受到了司法的强力挑战。1992年, 作为CAS仲裁案件上诉法院的瑞士联邦法院(the Swiss Federal Tribunal, SFT), 在德国马术运动员甘德尔诉国际马术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Equestrian Federation, FEI)上诉案中, 认为IOC是CAS的管理机构, FEI作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IOC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利害关系, CAS就FEI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做出的裁决缺乏让人信服的公信力。1994年, CAS在内部成立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CAS), 作为CAS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和业务监督部门。
1.2 CAS的组织结构
CAS由2个部门组成:一是主要行使管理职能的ICAS; 另一部门是为体育纠纷提供解决方案的CAS本身。根据《ICAS和CAS组成章程》第6条之规定, ICAS主要负责CAS的行政事务与财政管理, 还可以任命一定比例的仲裁员[4]。ICAS由20名在国际仲裁或体育管理等领域有一定造诣的国际法官或律师组成, 每一届履职周期为4年。在这20名成员中, 其中1人为ICAS主席, CAS普通仲裁部门主席和上诉仲裁部门主席兼任ICAS的副主席。ICAS成员在接受任命时必须签署声明, 承诺以个人身份完全客观和独立地行使职能。所有成员都不能在案件前阶段程序中担任该案仲裁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现任20名ICAS成员分别来自16国家, 包括欧洲9人, 北美洲4人, 亚洲、非洲、大洋洲各2人, 南美洲1人, 有6名曾是运动员。中国籍国际法院法官薛捍勤于2014年11月18日被任命为ICAS成员。
提供体育纠纷解决服务的CAS本身由普通仲裁部门和上诉仲裁部门组成, 以便明确区分一审仲裁案件和针对体育机构的决定引发的上诉纠纷。普通终裁部门负责裁决通过普通程序向CAS提起的纠纷; 上诉仲裁部门对不服体育组织的决定而提起的上诉进行裁决, 每个仲裁部门均设有1名主席。CAS目前在册仲裁员共有369名, 来自超过80个国家, 其中中国籍仲裁员8名。仲裁员的任期同样为4年, 他们一般都是精通体育法、仲裁法、国际仲裁法的专业人士。仲裁员不隶属于特定的CAS部门, 可以参与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仲裁员被任命时, 也必须签署一份内容为“完全客观和独立履行职能”的声明, 所有仲裁员都受保密义务的约束, 不得泄露任何与当事人、争议案件本身有关的信息。
为了便于当事人听审、拓展国际业务、扩大全球影响力, 1996年, CAS在美国丹佛(丹佛办事处于1999年12月搬至美国纽约)和澳大利亚悉尼设立了2个常驻办事处, 这2个办事处受理仲裁申请和处理所有程序性行为。办事处由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职员进行运作, 他们根据仲裁规则, 结合案例自身特点、参考当事人要求进行仲裁。同时, CAS与阿联酋阿布扎比、中国上海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相关部门和组织开展合作, 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听证中心, 以便在此使用场馆和开展服务。
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大型国际性比赛促进了CAS的发展, 在这些比赛中出现的体育争议不仅数量越来越多, 涉及面越来越广, 案情也越来越复杂。为了及时、快速地解决大型比赛产生的纠纷, CAS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设置临时仲裁庭(Ad Hoc Division, AHD)。AHD以快速、公平、经济地解决纠纷为宗旨, 是CAS处理体育竞技型纠纷、管理型纠纷的集中场所。根据《奥运会比赛仲裁规则》第1条要求, AHD能够行使管辖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 纠纷发生在奥运会比赛期间或奥运会开幕式前10 d内; ② 针对IOC、NOC、IFs或奥运会组委会所做决定提出的仲裁申请, 要求申请人在向CAS提出申请前必须穷尽内部救济程序。夏季奥运会AHD一般由1名主席和12名仲裁员组成; 冬季奥运会AHD一般由1名主席和6名仲裁员组成。鉴于兴奋剂问题越发严重, CAS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设CAS反兴奋剂特别部门, 专就奥运会比赛期间或奥运会开幕式前10 d内出现的兴奋剂纠纷进行管辖, 该部门在里约奥运会中共办理了8件兴奋剂案件。
2. CAS仲裁体系的发展困境
2.1 CAS典型案例分析
2.1.1 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诉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案[5]
申请人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是有史以来德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女子速度滑冰运动员, 她一共获得9枚奥运会奖牌, 其中金牌5枚。第1被申请人是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the Deutscher Olympischer Sportbund, DOSB), 第2被申请人是IOC。2009年2月4日—4月30日, 作为血液剖析程序的一项内容, 国际滑冰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ISU)向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采集了90余份血液样本, 以供为其编制“生物护照”(运动员的生物护照是为专业运动员编制的个人的电子数据记录。在一段期间内对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结果进行整理, 对运动员的各项身体指标进行记录。生物护照会长期跟踪记录运动员的血液指标, 如果该指标出现超出允许限度内的异常变化, 则表示该运动员有违规的可能), 方便随时监测她的生物学特性变化, 从而更容易检测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2009年2月哈马尔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期间收集到的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血液样本结果显示, 其中一些指标超出了其“生物护照”允许的正常波动范围。2009年7月1日, ISU纪律委员会(the ISU Disciplinary Commission)决定从2009年2月9日开始对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禁赛2年。2010年2月15日, 申请人于温哥华冬奥会前向AHD提交仲裁申请, 并提供其因为遗传性血液疾病导致血液样本检测存在异常的证据, 请求仲裁庭裁决:① 第1被申请人DOSB提名其参加温哥华冬季会女子速度滑冰项目; ② 第2被申请人IOC同意其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AHD随后裁定:① AHD对本案无管辖权; ② 驳回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的仲裁申请。申请人随后向瑞士联邦法院申请的上诉也遭到驳回。
在体育纠纷解决系统中频频受挫的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转而寻求国家司法机关的帮助, 慕尼黑高级法院审理后认为申请人和ISU之间的仲裁协议违背了《德国反垄断法》(German anti-trust law)之规定, 强制性的仲裁协议与德国公共政策明显相悖。法院的裁决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推论上:包括IOC、IFs在内的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垄断性地控制了国际性体育比赛, 对于以参加比赛为生存方式、工作方式的职业或专业运动员而言, 他们不得不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制定的任何规则, 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垄断部门的性质和特点。《德国反垄断法》明确禁止处于支配地位的组织施加比一般合同规范更严苛的限制条件, 如ISU要求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只有签署CAS排他性管辖的仲裁协议才能参加比赛的行为违反了上述禁令要求。
2.1.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纳辛纳辛·亚达夫、印度国家反兴奋剂机构案[6]
本案发生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 申请人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 第1被申请人纳辛·亚达夫是一名印度摔跤运动员, 他于2016年7月15日被确认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印度警方调查后认定纳辛·亚达夫因被竞争对手在其饮料里投放违禁物质而造成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之事实。2016年8月1日, 第2被申请人印度国家反兴奋剂机构(the National Anti-Doping Agency, NADA)采认警方调查结果, 认为纳辛·亚达夫不存在过错或疏忽, 裁定他并未违反《印度国家反兴奋剂条例》。WADA于2016年8月13日向里约奥运会AHD提交申请, 请求裁定:① 纳辛·亚达夫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要求对其禁赛4年; ② 纳辛·亚达夫在2016年6月25日后取得的比赛成绩无效。第2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 认为WADA在2016年7月23日针对本案召开的听证会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而故意等至AHD管辖期开始后才提出申请, 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违反禁反言原则(禁反言原则是人们在进行诉讼行为时, 应对自己以言词做出的各种表示负责, 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 认为AHD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之首要问题是确定AHD是否有管辖权, 里约奥运会AHD的管辖期为2016年7月26日—8月21日。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 虽然对第1被申请人的兴奋剂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时间均发生在AHD管辖期间外, 但NADA做出的第1被申请人未违反《印度国家反兴奋剂条例》的决定却发生在管辖期内, 而申请人也是对此项裁定提出异议, 因此AHD具有当然管辖权。关于第1被申请人提出自己被人故意添加违禁物质的抗辩, 仲裁庭并未采信印度警方的调查结论, 认为被申请方提供的4名证人的证人证言均属于间接证据, 只能证明纳辛·亚达夫的抗辩理由是“可能的, 但并不是高概率的或明确的事实”, 他们更愿意相信申请人提供的专家证人所做的专业解释, 仲裁庭最终裁决纳辛·亚达夫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2.2 CAS仲裁体系发展困境之成因
2.2.1 组织结构设计失衡, 违背社会首要价值之“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 正义主要用于人的行为, 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 “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于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 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7]。任何事物是否正义的首要前提是背景制度是否正义, CAS的经济来源情况和仲裁体系组成结构却暴露出其缺乏独立性、中立性。
(1) 仲裁员国籍分布失衡。CAS成立之初大部分业务来源于欧洲, 其工作语言也是英语和法语, 最初出于便利工作之虑和由于语言所限, 大部分仲裁员也都来自欧美及大洋洲, 但是发展至今日, CAS的业务来自世界各国, 若一味固守区域偏好甚至偏见, 长期如此, 其裁决恐难服众。在目前的仲裁员名单中, 美国46人, 瑞士33人, 英国29人, 澳大利亚26人, 德国18人, 加拿大16人, 意大利13人, 西班牙12人, 这8个国家的仲裁员人数占到了52.3%, 而其他体育大国如中国有8人, 日本有2人, 俄罗斯有1人[8], 仲裁员国籍分布明显失衡。
(2) CAS财政供给除了当事人缴纳的仲裁费、调解费或咨询费外, 更多来源于IOC、IFs、NOC等(以下笼统称为“官方机构”)组织给予的经济支持, 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导致双方存在无法忽视的利害关系。
(3)“官方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了负有管理义务的ICAS委员的委任权。根据《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第4条之规定, 20名ICAS委员构成如下:IOC、IFs、NOC各有4名提名权, 4名由上述12名成员协商后选任, 最后4名由上述16名成员委任。另外, ICAS现任主席是IOC副主席澳大利亚人约翰·科茨, 其关系之复杂可见一斑。
(4)“官方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了掌握裁判职能的仲裁员的选任权。根据《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第14条规定, “官方机构”有权提名仲裁员, ICAS最后对仲裁员名单予以确定。
(5) 具体案件的仲裁庭组成亦受“官方机构”约束。根据《国际体育仲裁员仲裁规则》第40条第2款之规定, 如果适用独任仲裁庭, 当事人应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协商决定。如果协商不成, 则由普通仲裁部门主席或上诉仲裁部门主席选任; 如果适用3人组成的合议庭, 双方当事人均可选任1名仲裁员, 随后这2名仲裁员选择第3名仲裁员同时该名仲裁员兼任仲裁庭主席。若当事人未达成合意, 则普通仲裁部门主席或上诉仲裁部门主席有权对仲裁庭主席予以任命。
2.2.2 司法介入力度失当, 缺乏对仲裁的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
CAS的仲裁权含有强制性和排他属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公权力。在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诉德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案中, CAS和瑞士联邦法院在并未对申请人提出的遗传性血液疾病导致血液样本存在异常的有力证据进行实质审理的情况下, 便驳回申请人申请, 难达实体正义。国家对要求行业自治的体育领域管控不断减弱, 但体育领域内部出现了更多的冲突和争议, 仅仅依靠包括CAS仲裁体系和体育协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难以保障相关人的权益, 特别是弱势一方的权益, 因此, 引入外部性的司法审查逐渐成为必要。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国家司法系统寻求帮助, 并在2015年获得胜诉, 虽然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6年, 但就像她说的那样:“每个运动员都可以在CAS和国家司法权之间进行选择, 我的胜利也许来得有点晚, 但今天我在用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 就像我在比赛中改变历史一样。”[5]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纳辛纳辛·亚达夫、印度国家反兴奋剂机构案中, CAS同样基于自己认为的“合法”原因不顾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具有司法权属性的印度警方之认定结果, 似乎从中可以推论:在CAS仲裁系统内, 尚未形成司法权和仲裁权的角力。CAS几近完全排除其他公权力介入的方式导致实践中产生大量不公正现象。
2.2.3 CAS仲裁规则失范, 直接损害运动员仲裁权益
(1) 排他性强制仲裁协议侵犯运动员程序选择权。运动员和“官方机构”间的仲裁协议一般有2种签订方式:一是运动员在加入该组织时被要求遵守带有解决纠纷仲裁协议的章程; 二是在参加大型比赛时, 主办方要求参赛运动员签署写有仲裁条款的准入表。不管采取何种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当事人间不容协商。如在奥运会前, IOC通过事先签署准入表的方法, 确定有关体育争议交由CAS行使排他性管辖权。运动员只有选择参加比赛或退出比赛之自由, 却无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也无选择纠纷解决机构之权利。“要么接受要么离开”之规则无须考虑运动员之真实纠纷解决意愿, “离开”对任何一名以参加奥运会为职业目标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选项。从自由权角度讲, 人的尊严意味着自主性与自决性[9], 普遍适用强制性仲裁条款将会产生如下2个方面的问题:① 降低运动员一方对CAS仲裁制度的信任度; ② 使得CAS仲裁制度有成为解决体育纠纷唯一方式之势, 可能导致CAS缺少竞争动力, 不利于其进一步完善。
另外, 排他性管辖权赋予仲裁庭过度自由裁量权, 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同案不同判”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主要是弱势运动员一方的利益。在纳辛·亚达夫案中, 仲裁庭以国内反兴奋剂机构作出决定的时间为双方纠纷发生日, 而同样是里约奥运会AHD处理的伊哈卜·艾哈迈德与埃及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纠纷一案中[10], 该案仲裁庭援引Joseph Ward v.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案[11], 认为应以涉嫌违纪运动员正式得到被禁赛通知为纠纷发生日。同届奥运会AHD在处理情况类似之案件, 一案仲裁庭采取“造法”, 一案仲裁庭遵循先例, 进行了不同的仲裁解释, 最后均获得了“理所当然”的管辖权, 仲裁庭最终也做出不利于运动员一方的裁决。
(2)“任意适用先例”侵犯运动员期待利益。公正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与平等形式相结合, 即相同的案情得到相同的判决(因此不同的案情应得到不同的判决)这一规律形式相结合。简单而言, 人们也可以把公正描述为判决的前后一致性。然而, CAS一方面并未正式表明将裁决先例作为仲裁规则的渊源, 另一方面却在裁决书中“任意”地援用先例。1986—2003年, 只有约1/6的CAS裁决书引用了先例; 而从2003年开始, “几乎每一个裁决书都会包含一个或者更多CAS裁决先例”[12]。不具有约束力的任意适用先例不仅会使得裁决远离正义, 同时会直接损害弱势一方即运动员的利益。“官方机构”控制仲裁员选任权, 经常参与仲裁程序的他们更了解仲裁员个人的裁决偏好, 他们在选择仲裁员时往往能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达致自己想要的“正义”。
虽然法官在裁判案件的司法过程中, 可以以公平、正义、合理、道德、情势变迁等为依据, 改变固有的法律规则, 或创建新的法律规则[13], 但如上文所述的在同一届奥运会中, 一仲裁庭正合“官方机构”心意而选择造法, 另一仲裁庭同样正合“官方机构”心意选择遵循先例。一方面, 法的确定性原则要求判决是在现行法律秩序内自洽地做出。现行法律是一张由过去的立法决定和司法决定或者习惯法的种种传统所构成的不透明网络的产物, 法的种种建制史构成了每个当代的判决实践的背景。另一方面, 合法性的主张要求判决不仅与过去类似案例的处理一致、与现行法律制度相符合, 而且也应该在有关问题上得到合理论证, 从而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把它作为合理的东西而加以接受。在一种当下的未来视域中判决实际案例的法官, 是以合法的规则原则而主张其判决的有效性[14]。
(3) 兴奋剂纠纷适用严格责任制度侵犯运动员一方举证权。包括仲裁在内的裁判活动, 归责原则适用于直接关系双方当事人之胜败。CAS在兴奋剂案件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即在运动员的体内发现禁用物质或发现其使用禁止方法就足以构成违规, 而无须考虑违规者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结果。因此, 运动员在涉嫌违规后, 根本无须进行罪轻、主观过错程度、客观危害大小等证据的举证, 这从另一角度便直接剥夺了运动员的举证权。举证责任的本质有2个属性, 除了诉讼负担, 举证权是其第2个属性。从法理上讲, 当事人享有通过包括仲裁手段在内的方式寻求保护权益、解决纠纷的权利。提供证据是当事人行使权利、维护实体权益最重要的手段, 当事人为了避免裁判之不利后果, 只有当举证作为权利被行使时, 它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严格责任制度对运动员个体而言极度不公平, 如尽管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提供了因为遗传性血液疾病而导致血液样本存在异常的科学证据, 但包括CAS在内的仲裁机构、瑞士联邦法院并未对无罪证据进行核实, 直接驳回申请人请求。尽管印度警方、印度反兴奋剂机构均认可亚达夫因被人投放违禁物质而主观无过错, 不存在违规行为, 但CAS仲裁庭固守严格责任原则, 进而支持WADA的请求。毫无余地的严格责任原则对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运动员而言, 面临着难以担负的压力和危险, 兴奋剂问题更像是体育领域的刑事纠纷, 然而仲裁庭只“挥挥法槌”便能结束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显然不合一般人之认识规则。
3. 我国体育仲裁体系构建的初步设想
3.1 保证仲裁组织结构设计合理
(1) 在仲裁机构上, 设置独立于体育行会的专业性体育仲裁机构。鉴于当前专业体育仲裁人员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 现阶段可以先依托其他较成熟的仲裁机构予以过渡性建构。如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IETAC)经过60年的发展, 已有一套较为健全的制度和较为完备的硬件设施, 并在深圳、上海、重庆等7地设有分会。其仲裁员有1 235人, 专业特长为体育法的仲裁员有10人, 2015年受案数已达1 968件[15]。而且, CIETAC有着丰富的运行专业仲裁部门的经验, 它目前已经设置了粮食行业争议中心、商业专业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等专业仲裁机构。关于过渡性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置, 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牵头, 在CIETAC框架内设置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 在具体结构设置上, 由CIETAC建立专门的仲裁员名册, 制定专门的《体育纠纷仲裁规则》。当在建立仲裁员名册时, 要均衡分配体育管理机构、运动员、CIETAC三者之间的提名权比重。由于仲裁庭的组成一般需要当事人在较短时间内做出选择, 对信息不对等的运动员个体而言, 即兴的选择可能造成实质不平等, 因此可常设独立的组织代表运动员进行选择。该组织组成人员应由运动员决定, 最好由具有一定的法律或体育背景的人担任, 可以是退役的运动员、兼职律师、其他社会人士等。该组织在仲裁过程中与“官方机构”对立, 以保证运动员最优利益为中心, 被赋予代表运动员选择仲裁员之权利, 确保运动员平等代表以获公正。
(2) 明确仲裁员在任期内必须专职, 不允许同时兼任律师。作为“自己的程序(即仲裁程序)的主人”的仲裁员, 在仲裁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制度设计时应当进一步明确仲裁员的责任机制。由于仲裁特有的民间性, 结合我国缺乏商业传统、现代仲裁理念和完善的诚信意识之现状, 对仲裁员的权力仍然特别需要制衡。如能建立有效的仲裁员责任机制, 必然会使仲裁员更加谨慎敬业, 当事人也会对仲裁这种方式更加认同。仲裁员的责任应当包括契约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这3种形式。
3.2 确保司法合理渗透
探讨司法力对仲裁进行渗透的合理性, 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入手。在主观方面, 仲裁自身的软弱性是关键因素。与诉讼相比, 仲裁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导致其带有一定的软弱性, 体现为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司法公权力保障自身程序的顺利进行。在客观方面, 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 每一个历史时期所强调的主价值观是变动的。从现代社会形成以来, 权利观念的发展就经历了从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与自由至上, 逐渐转向社会本位、法律更多地强调社会公共利益, 最后发展到现今强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兼顾与平衡。国家出于协调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防止仲裁过程中出现损害国家、集体或某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以及防止个人过度自由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的考虑, 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 当然地要对当事人的自治进行司法限制和监督。
对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是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都明确规定了法院有权对各级仲裁机构的仲裁进行司法监督。体育仲裁是将商事仲裁纠纷解决方式引入体育领域的体现。在司法监督方面, 体育仲裁必须遵循《仲裁法》关于司法监督的基本规定, 同时应结合体育纠纷之特质, 确立独特的司法监督制度。在司法力与体育仲裁之间关系的定位上, 应努力寻求两者的平衡, 仲裁的自治性与司法力对其的渗透应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天平”要求得平衡, 必须依赖两者之间力量的均衡, 而这种均衡的实现, 最终将取决于司法力对仲裁进行渗透的合理度的设计和实行。正所谓“我们始终在寻找自由与限制和谐发展的状态”[16]。“若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CAS未提供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情况下, 司法机关作为体育自治的监督部门, 应给予适当司法干预, 以利于实体正义之实现”[17]。当然体育仲裁处理的体育纠纷大部分涉及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 过度介入或有不尊重体育自治、不尊重体育个性之患, 但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或者至少在“自然正义”是否被遵守、当事人确定的法律仲裁协议是否有效、裁决事实的是非曲直是否正确这一系列问题应当加强司法审查, 毕竟仲裁员特别是明显具有行政属性的体育仲裁员有错判乃至枉法的可能性, 对体育仲裁的司法审查是对遭受不公正裁决的当事人之最后救济手段。
3.3 仲裁合意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强制色彩为补充
体育仲裁虽有其特殊性, 但亦是仲裁制度在体育领域的展现。世界各国和地区仲裁法以及仲裁相关规则关于三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共同特点:① 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② 明确规定选定仲裁员是当事人和当事人委任的仲裁员的法定责任, 体现了在仲裁庭组成上的当事人主义, 而非由仲裁机构或法院主导; ③ 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规定详细具体, 特别是在三人仲裁庭的组成和首席仲裁员的产生上规定得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层次分明; ④ 不仅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而且体现了仲裁效率原则, 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具有科学性。
体育仲裁特别强调时效性, 大型运动会中发生的纠纷更需要在24 h内解决, 过多考虑当事人的意愿, 必然浪费过多时间, 但对时效性的追求不能以违背当事人意愿为代价, 类似格式合同的体育仲裁协议都在纠纷发生前做出, 对运动员而言, “无法拒绝”的同意意味着将面临巨大风险。如CAS仲裁体系中, 往往最后皆由普通仲裁部门主席或上诉仲裁部门主席确定首席仲裁员, 双方当事人悬殊的实力对比使得强者总是能依靠自身地位给予弱势一方潜在压力以迫使其放弃诸多权利, 仲裁裁决无法达致实体的妥当性和程序的合法性。我国的体育仲裁不应简单地根据管辖规则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开始仲裁程序, 相反, 仲裁庭应主动审查双方是否形成合意。仲裁庭需要特别关注一些焦点, 审查和确保运动员个体是否真实同意仲裁协议中关于适用更高标准的条款, 双方是否已达成一致仲裁协议。只有双方均表示认可的、可仲裁的争议, 仲裁庭才享有管辖权。
3.4 尊重合理期待原则
德沃金法律哲学的核心主张——“法律作为原则一贯性”向来被视为一种法律的融贯论。原则一贯性作为立法原则, 它要求立法者必须试图使其所指定的法律在道德上是融贯的; 原则一贯性作为裁判原则, 则要求法官尽可能地将法律视为一组融贯的原则所构成的整体, 即法律要尊重当事人的合理期待, 遵循先例制度的确定即是尊重合理期待的体现。体育纠纷主要分为:① 竞争型体育纠纷, 主要是指发生在运动员、裁判员、体育组织之间的纠纷; ② 合同型体育纠纷, 指在各种非行政身份的体育组织和竞技人员等主体地位平等的双方在参加体育比赛和其他活动时发生的违约、不完全履行合同等纠纷; ③ 管理型体育纠纷, 是指有行政管理权的一方为当事人的纠纷。有人认为, 以遵循先例为确定原则势必会削弱仲裁的私人性质, 遵循先例所要求的裁决公开也定会侵犯隐私, 亦可能固化规则适用。此类担忧主要针对合同型体育纠纷, 在双方当事人具有直接或间接隶属关系的竞争型和管理型体育纠纷中, 有必要进行利益权衡。
现代功用主义奠基者、英格兰哲学家边沁尊崇“法律可知”和“司法共享”, 提出“正义以预期为基础”, 遵循先例即提供了预期, 他甚至认为即便是合乎事宜、时宜的法官造法也会破坏公众对法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的信任。CAS目前适用先例“法律一致性有时出现”(legal coherence sometimes suffers)只会主观不均衡地损害运动员个体利益。我国的体育仲裁立法者无须担心遵循先例或许会导致裁决做出过程充满僵化, 因为连续性和变化均是遵循先例的应有之义, 相较于“任意适用先例”的激变和频繁变化, 仲裁员应辅以善意、理性、平衡良心原则适用先例, 毕竟遵循先例原则可限制仲裁员裁决恣意, 增进仲裁规则的确定性、安全性和可预测性。法律维持秩序的功能之独特性在于, 人们可以合法地对他人(和对自己)有什么期望, 抱什么样的期望才是得体的, 期望的不可靠比经受意外和失望更让人无法承受。
3.5 保障当事人之充分参审权
随着社会经济情势之急速变迁, 体育仲裁之质、量多异于往昔, 形态、内容上亦趋于多样化、复杂化。从CAS近年来案件激增及仲裁结果看, 此种变化不但实际上扩大了纷争解决过程之困难度, 同时, 由于一般运动员之权利意识已更为高涨, 当事人对于仲裁制度越感不满, 则将越趋向于逃避其使用。虽然仲裁裁决犹如法院之裁判, 必然会驳斥一方当事人并采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 在此种制度构造下, 引发一方当事人对裁决不满的现象, 亦属于常理。CAS仲裁体系在处理兴奋剂案件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相当于间接剥夺了运动员一方的举证权和听审权, 未充分参与审理导致当事方对裁决越发不满。当事人将仲裁权力移交给仲裁机构的前提是仲裁机构必须确保当事人各项程序性权利都能得以正确行使。并且, 诚如历来实务经验所示, 诉讼当事人对于其曾亲自参与之裁判过程越能信服、满足, 则其自动自发顺从裁判内容所示纷争解决方案的概率越高, 此乃当事人更能接纳裁判结果之表征。
在构思如何充实程序制度之际, 不应仅以本案判决可能具有执行力或既判力为由, 遂认为仲裁制度已充分发挥其解决纠纷之功能。换言之, 致力于经由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运作, 促使当事人更加信赖、信服、接纳裁判或其他纷争处理之结论, 进而自动予以履行, 仍属值得追求的目标。基于此认识, 为提升裁判制度或其纷争解决制度的使用者、参与者对裁判或纷争处理过程及其结果的信服度、接纳度, 应重塑仲裁公信力, 并使程序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机能。
我国在进行体育仲裁制度设计时, 首先应保障运动员一方之举证权, 倘若运动员能提供“违禁物质”无法提高自身运动成绩或自己主观不存在过错之有效证明, 就不应对其进行惩罚。其次在证明责任及举证分配上应以过错推定原则为主, 同时为达致个案公平而采取灵活归责原则。其他归责原则可能包括武器平等原则、危险领域理论、盖然性理论、证据接近度、证据之可及性、诚信原则等。根据个案的特性, 应适用混合模式以弹性克服僵化, 保证实质正义之实现。如在举证过程中, 包括中国奥委会、各体育协会等体育组织负有检测过程合乎正当程序、检测人员具有相应资质、样品保管无过失等事项的证明责任。根据证据接近度原则, 宜将主观过错程度之证明责任分配予涉药方, 因其在时间、空间上更易掌握相关证据, 若其无法提供或故意不提供, 则可推定其主观存在过错, 此乃过错推定责任之运用。灵活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修正了严格责任原则之缺陷, 使得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能够充分亲历仲裁过程, 有利于提高裁决结果的可信度和接纳度。
4. 结束语
我国在进行体育仲裁制度设计时, 应首先遵循《仲裁法》的基本原则, 同时基于体育仲裁的特殊性予以个别化、专门化设计。除了建立独立的、专门的仲裁机构外, 为了达致纠纷解决之连贯性, 在纵向层面应参照CAS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经验, 在国内各体育协会制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建立自身的纠纷解决部门, 以迅速处理领域内的体育纠纷; 同时, 在横向层面应注意与外部专门体育仲裁机构有效衔接, 即在穷尽内部救济后, 当事人可将纠纷提交外部专门体育仲裁机构予以处理。另外, 可以参照CAS仲裁体系中常设仲裁庭和临时仲裁庭之双元设置模式, 向全国大型运动会如全运会等比赛派驻临时仲裁机构, 以及时、快速、有效地解决争议, 保障体育比赛之持续性、精彩度, 助力体育运动持续、健康发展。
-
[1] 搜狐公众平台. 图说: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况[EB/OL]. [2016-12-29]. http://mt.sohu.com/20150827/n419863221.shtml [2]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2015年体育产业统计数据[EB/OL]. [2016-12-29]. http://www.sport.gov.cn/n10503/c782559/content.html [3] 布莱克肖. 体育纠纷的调解解读[M]. 郭树理, 译.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 1 [4] CAS.Statutes of ICAS and CAS[EB/OL].[2016-12-29].http://www.tas-cas.org/en/icas/code-statutes-of-icas-and-cas.html
[5] Matt S.Claudia pechstein puts sport's supreme court on trial[EB/OL].[2016-12-31].http://www.bbc.com/sport/31447368
[6] CAS.World Anti Doping Agency v. NarsinghYadav[EB/OL].[2016-12-30].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OG%2016-025.pdf#search=Narsingh%20Yadav
[7]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8] CAS.List of arbitrators (general list)[EB/OL].[2016-12-30].http://www.tas-cas.org/en/arbitration/list-of-arbitrators-general-list.html?GenSlct=2&nmIpt=&nltSlc%5B%5D=176
[9] 陈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6 [10] CAS.IhabAbdelrahman v. Egyptian NADO[EB/OL].[2016-12-30].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OG%2016-023.pdf#search=Ihab%20Abdelrahman
[11] CAS.Joseph Ward v.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EB/OL].[2016-12-30].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OG%2012-002.pdf#search=Joseph%20Ward
[12] Zachary G.Athletes have rights too, right?Investigating the extreme unfairness insports'purported supreme authority wh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fails to reign supreme[J].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6, 24:409
[13] 崔林林.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英美司法风格差异及其成因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 [14]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45 [15]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贸仲简介[EB/OL]. [2017-01-03]. http://www.cietac.org/index.php?m=Page&a=index&id=2 [16] 卡多佐. 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 董炯, 彭冰,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165 [17] Jason G.The Olympic binding arbitration clause an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An analysis of due process concerns[J].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2008, 18:1017-1022 http://ir.lawnet.fordham.edu/iplj/vol18/iss4/4/
-
期刊类型引用(4)
1. 于良东. 我国竞技体育仲裁机制的现状检视与路径优化. 重庆行政. 2024(02): 71-73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李智.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法学. 2022(02): 162-17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刘韵.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兼评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 中国体育科技. 2022(09): 88-9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李敬平. 运动员权益发展现状研究综述.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21(03): 166-16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41
- HTML全文浏览量: 86
- PDF下载量: 12
- 被引次数: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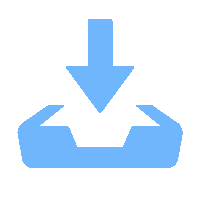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