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s to the IOC's Governance During Thomas Bach's Presidency: Intense Institutional Work to Achieve Balance and Compromise
-
摘要:
近年来,传播、文化、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的变化影响了国际奥委会(IOC)的运作方式及其系统治理、政治治理和组织治理,使国际体育环境更加复杂且更具挑战性,并导致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性危机。自2013年托马斯·巴赫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为应对这一危机,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化运作以谋求平衡和妥协,加强其对世界体育的领导:采取善治举措,包括制定清晰的战略路线、巩固商业模式、采用新治理原则和机制等;通过彰显体育的积极影响应对质疑,主要集中在可持续性、通过体育促进发展以及奥运会的积极遗产等3个方面。托马斯·巴赫的战略结合了对各种力量的审慎评估和巧妙的风险管理,可被视为一种现实政治,与新制度社会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
Abstract:Recent changes in broadcasting, culture, economics,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have affected both the wa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operates and its systemic,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changes have created a more complex and more challenging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led to a crisis of legitimacy for the IOC. Drastic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has hence been conducted to achieve balance and compromise by IOC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its leadership of world sport,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since Thomas Bach was elected president in 2013. That is, "good governance" was taken, which included designing clear strategy route, solidifying commercial modes, using new governance principle and mechanism, etc. And, the active influence of sport was highlight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whi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sustenance,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through sport and positive legacy of Olympics. Bach's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careful assessment of the forces in play and deft risk management, can be considered a form of realpolitik, with similarities with neo-institutional sociological theories.
-
皮埃尔·德·顾拜旦于1894年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其作为国际主义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塑造“体育骑士精英”[1]。即使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经济全球化,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在当今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中仍须不断调整以确保其合法性。国际奥委会通常是指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多达115名成员组成的俱乐部,以及一个设在洛桑总部的行政办公室。事实上,作为世界体育的领导机构,国际奥委会比这更为复杂:首先,在过去20年中,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团(被称为国际奥委会集团),由一个非营利组织领导,旗下有几家商业公司和基金会。其次,它拥有奥运会的所有权,奥运会由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 OCOGs)通过主办城市合同与国际奥委会签约举办。再次,国际奥委会与合作伙伴共同监督奥林匹克运动,其因管理公共体育并与举办奥运会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依赖而被Chappelet[2−3]称为“奥林匹克体系”。该体系包括各国家(地区)奥委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NOCs)、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s, NFs)及其运动员、历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最后,国际奥委会与其合作伙伴共同承担在全社会弘扬奥林匹克主义的使命。
为了分析托马斯·巴赫对国际奥委会治理变革的影响,笔者基于文献综述及对6位学者(高管)的访谈——3位学者专门研究奥林匹克历史与地缘政治、国际体育、体育诚信以及奥林匹克治理,另外3位高管分别来自奥运会夏季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Association of Summer Olympi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ASOIF)、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Glob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GAISF)和国际奥委会。根据Huberman等[4]关于归纳性定性研究的建议,笔者请这些专家对围绕国际奥委会治理的论述进行分析。例如,笔者描述了托马斯·巴赫领导下国际奥委会治理的具体变化,并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笔者的描述,如果不同意,则请他们给出意见。
笔者将这些访谈内容与从有关国际体育和奥运会的专业文献、国际奥委会网站(自2014年以来的国际奥委会报告,国际奥委会于2014年和2021年发布的2个议程等)、专家报告(ASOIF 2020[5],ASOIF 2017—2022[6],透明国际2016[7]等)、有关体育治理的国际研究项目(Geeraert 2018[8],Play the Game发布的报告/分析,如Weinreich 2020[9])以及国际体育/奥运会治理专业网站(尤其是Insidethegames)收集的数据相结合。笔者还从瑞士国家研究基金(2014—2018年、2020—2024年)资助的2个关于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治理和绩效管理的研究项目中获得了数据。本文采用的建构主义视角以及其他学者[10]在这一主题上提出的观点均涉及在具体语境下分析行动者的行动和策略,因为这些行动和策略只有在它们被部署的背景和语境中才有意义。因此,笔者使用经济(收入的来源、类型和数量)、法律(法律框架和监管工具)、社会(与体育有关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政策和政治工具)等方面的事实和指标,以分析参与者在其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学背景下的战略。以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可能预示着合法性危机[11],这种危机可能导致新形式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是确保一个组织或系统生存或成功所必需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化以及传播、文化、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方面的重大变化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托马斯·巴赫的领导下,国际奥委会综合运用了系统、政治和组织治理工具,试图克服这些挑战并保持其在国际体育领域的领导地位。通过分析这3种治理类型,可深入了解国际奥委会如何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危机调整其政策以及与利益相关方互动。托马斯·巴赫自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所采取的战略是一种现实政治,它建立在对各种力量的审慎评估和巧妙的风险管理之上。本文讨论托马斯·巴赫的现实政治方法(旨在保护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性)与新制度社会学理论(关于一个部门内如何发生变化)之间可能的相似之处。
1. 三种相互关联的国际奥委会治理形式
为了理解奥林匹克体系如何运作,有必要考察国际奥委会如何使用组织、政治和系统治理[12]影响并尽可能控制其4个主要利益相关方(NOCs、IFs、NFs和OCOGs)。组织治理描述了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使用的决策和政策执行机制(结构、程序、权力博弈),国际奥委会的3个主要目标是发展体育、实现财务目标和通过体育造福社会[13];政治治理决定了一个组织与政治的关系,国际奥委会的政治关系影响着各国政府和超国家联盟利用监管、财政和道德机制影响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体系的方式,也影响着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体系利用体育事业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系统治理涉及通过共识/妥协和共享权力来调节/协调网络,而不是通过强制措施来调节/协调行动,一些体育领域的专家将此称为“伙伴关系”、“共享”或协作治理[14],国际奥委会借助系统治理手段将其愿景强加于奥林匹克体系,由于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和种类(公共、非营利、商业组织等)繁多,国际形势不确定,以及需要地方和全球协调,这项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
1.1 系统治理
据《奥林匹克宪章(2021年版)》所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通过体育教育青年,为建设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因此,举办奥运会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国际奥委会历来呼吁核心合作伙伴举办奥运会,发展体育运动,弘扬“卓越、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根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设定的标准和分配给它的运动员配额,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根据标准选拔精英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国家(地区)奥委会派出运动员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奥运会由奥组委组织,奥组委则由东道主的体育运动和公共机构(主办城市、主办地区、主办州)共同管理,但受到国际奥委会日益详细的奥运会规程和资金分配方案的密切控制。
在资金方面,奥运会不断增长的收入让国际奥委会得以宣称其“将90%的收入重新分配给了更广泛的体育项目”[15]。 这些资金以4年为周期重新分配,其中:50%分配给夏奥会和冬奥会的组织委员会;38%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奥林匹克团结基金;12%分配给青奥会和体育诚信
1 机构,特别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 Doping Agency, WADA)。1992年,国际奥委会仅向25个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重新分配了3760 万美元,但电视转播权收入的飙升使国际奥委会在其后的20年里迅速增加了这一数额。因此,在 2016—2020 周期,国际奥委会向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重新分配了5.4亿美元,是1992年的14倍。不过,每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获得的金额取决于2004年引入的标准,以便国际奥委会将更多资金分配给知名度最高、营销潜力最大的体育项目(如田径、体操、游泳)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表1)。表 1 重新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大致金额(现金和实物)[16]Table 1. Approximate amounts redistributed to NOCs and Olympic IFs (cash and benefits in kind)亿美元 在此时间节点后重新分配 国家(地区)奥委会 奥林匹克项目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 3.01 2.97 伦敦2012年奥运会 5.20 5.20 里约热内卢2016年奥运会 5.40 5.40 东京2020奥运会 5.40 5.40 图灵2006年冬奥会 1.36 1.28 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 2.15 2.09 索契2014年冬奥会 1.99 1.99 平昌2018年冬奥会 2.15 2.15 新参与者(职业联盟、运动员联盟、非政府组织、社交网络等)的加入使奥林匹克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国际奥委会必须面对的利益相关者数量有所增加[3]。例如,国际奥委会必须说服职业联盟,尤其是北美的职业联盟,允许运动员参加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举办的世界锦标赛/杯赛和由其负责项目技术工作的奥运会。此外,在过去30年里,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之外的国际体育赛事数量激增,因此,现在的赛历还包括:①商业性综合体育赛事,例如世界极限运动会X Games、全球风筝运动协会(Global Kitesports Association, GKA)的Big Air世界锦标赛、国际极限运动节世界系列赛;②非营利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例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长者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世界城市运动会;③单项体育赛事,例如终极格斗锦标赛、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冲浪联赛、红牛赛事、铁人赛。此外,这些国际赛事和北美主要赛事联盟,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美国职业篮球大联盟(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北美职业冰球联盟(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等,都采取了全球营销战略。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期待,确保奥运会保持吸引力,国际奥委会在奥运项目中增加了几个新项目,如三人篮球(东京2020奥运会)和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2024年奥运会上取代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激流回旋项目)。运动攀岩、冲浪和滑板在巴黎2024年奥运会上仍是附加项目,但从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起将成为正式项目。长期以来,这些运动一直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成立新的国际攀岩联合会
2 或加入现有的世界轮滑总会3 而实现制度化。由世界运动舞蹈总会管理的霹雳舞是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第4个新增项目。然而,霹雳舞不会出现在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上,因为国际奥委会选择的5个项目——壁球、棍网球、腰旗橄榄球、棒球/垒球和板球——都与强大的封闭式联盟关系密切,特别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腰旗橄榄球)、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日本职业棒球联盟(棒球是日本的第一大运动),以及印度超级联赛(板球在印度极具统治力),这些都是体育商业模式的典型代表,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北美和亚洲这2个最重要市场的兴趣。为了给3个新项目腾出空间(夏季奥运会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
10500 人),国际奥委会减少了3个媒体关注度较低项目(赛艇、拳击和举重)的比赛分项和运动员人数。尽管拳击、举重和现代五项因管理不善和诚信缺失(兴奋剂、内讧、财务问题)而被质疑,但它们仍被保留在巴黎2024年奥运会和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项目中,只是运动员配额有所减少(如赛艇)。这些变化将使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数量从28个增加到31个,但新成立的联合会暂时不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资助。对于世界橄榄球总会(七人制橄榄球)和国际高尔夫球联合会而言,情况亦如此。七人制橄榄球和高尔夫在2016年成为正式奥林匹克项目。在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2026年冬奥会上,一个管理滑雪登山运动的新联盟将首次亮相。未将奥运收入重新分配给这些新项目是一个妥协后的决定,目的是安抚最古老的奥运项目,拨款不被减少。对国际奥委会而言,电子竞技是另一个仍在摸索中的新领域。通过给一个集游戏节、展览竞赛和论坛于一体的活动打上“奥林匹克”标签并将其命名为“奥林匹克电子竞技周”,国际奥委会迈出了整合电子竞技的第一步。该活动于2023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凸显了国际奥委会的矛盾立场,因为它只包括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关的游戏
4 ,尽管这些游戏远不如电子竞技的主要游戏(如“英雄联盟”“反恐精英”等)受欢迎。然而,托马斯·巴赫在2023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提醒说,全世界有30亿人在玩电子竞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新成立的奥林匹克电竞委员会研究创办一届电竞奥运会[17]。但是,为了遵守奥林匹克价值观,玩家必须射击物理目标,而不是射击具象的人物。为了保持其在这一复杂系统中的领导地位,国际奥委会必须建立联盟,抵御对其权威的挑战。这种挑战甚至可能来自其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内部,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公开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国际奥委会曾决定不向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支付报酬并且拒绝满足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Sport Accord)2015年提出的增加向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再分配金额的要求[18]。成立于2009年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代表所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过举办多项体育赛事(如世界沙滩运动会、世界搏击运动会)和维护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利益,成为国际奥委会强有力的抗衡力量。但是,“托马斯·巴赫最终在2017年成功地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取代了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从而拔掉了国际奥委会的这根刺”(来自对体育组织高管的访谈)。在2022年底,托马斯·巴赫成功解散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并将代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重要职能交还给了改组后由国际奥委会控制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而后者目前只负责举办国际体育运动联合会年度大会[19]。
在过去20年里,精英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受到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公众越来越严密的监督,尤其是在诚信、运动员福祉、人权和可持续性方面。作为回应,国际奥委会试图通过引入新的监管机制来打击兴奋剂、暴力、种族主义、操纵比赛和腐败,从而避免来自这些方面的批评。为此,国际奥委会不得不采取新的政治治理方法。
1.2 政治治理
政治治理涉及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联合国、欧盟、欧洲委员会、各国政府以及支持官方体育机构组织体育运动和举办体育赛事的城市/地区。这些关系往往围绕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展开,如政府抵制体育赛事、政府干预国家体育机构的管理、政权利用体育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工具等。与此同时,举办奥运会和为奥运会体育项目提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育界与公共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大多数奥运会体育项目依赖直接和间接的公共支持来资助体育设施建设、国家和地区(残)奥委会运转、俱乐部运行和精英运动员专业化程度提升。这种公共伙伴关系赋予了国际奥委会合法性,使其能够就奥运会的国家法律豁免权进行谈判:免税、保护联合会和运动员的立法、在奥运会期间适用“奥林匹克法规”。
同样,在法律领域,国际奥委会于1984年在洛桑设立了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以提供一个解决体育纠纷的机制,从而规避体育与国家司法系统的相关风险(流程缓慢、媒体报道成本高、缺乏体育的特殊性)。所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甚至国际足联,现在都承认国际体育仲裁院,其谨慎而有效地解决了运动员与其联合会之间的许多内部纠纷。国际体育仲裁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涉及兴奋剂(约占60%)和足球(约占59%)。
由于有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现在很少有体育纠纷诉诸国家法院或超国家法院(欧洲法院),除非涉及刑事犯罪行为,则自动归刑事法院管辖[19]。在奥运会期间,国际体育仲裁院甚至会设立一个临时法庭。一些国家则设立了国家体育法庭以及其他调解和调停机制,以解决与体育有关的争端。
为了保护体育运动的公信力和运动员的健康免受兴奋剂之害,国际体育运动与各国政府于1999年联合成立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与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03年制定)有关的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处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鼓励各个国家建立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和地区反兴奋剂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国际反兴奋剂机构(Institute of National Anti-Doping Organisations, iNADO)网络的成员,尽管这些机构拥有的资源差别很大。然而,这些机制未能杜绝兴奋剂,俄罗斯运动员在国家支持下使用兴奋剂(特别是在索契2014年冬奥会上)就是明证[21]。面对采取行动反对俄罗斯的巨大压力,国际奥委会暂停了俄罗斯国家奥委会参加2016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奥运会的资格,但随后淡化了制裁,允许符合国际奥委会规定标准的俄罗斯运动员以奥林匹克旗帜为标志参赛[22]。国际反兴奋剂检测机构(ITA)于2018年成立,目的是在某些运动项目,特别是那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模较小、自身反兴奋剂体系不完善的项目中,提供更加独立(独立于国家政府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反兴奋剂控制。与诚信、廉洁相关的危机也影响了许多较大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如田径、足球、网球、冬季两项),并导致其中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21世纪以来陆续建立起内部诚信组织(第一个是2008年成立的网球诚信组织)。这些组织的职权范围各不相同,通常涵盖对各类违反体育诚信行为的治理,包括操纵比赛行为、对运动员的心理/性骚扰、暴力、种族主义和腐败行为以及兴奋剂违规行为。国际奥委会的廉正战略较为分散。例如,国际奥委会在2022年成立了一个“安全体育”部门[23],专门负责处理运动员受到骚扰的问题。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士成立了国家体育诚信机构,负责监督所有与诚信相关的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这些机构往往主要关注兴奋剂问题。
许多案件——最著名的是1995年的博斯曼裁决——突出了在尝试将体育的特殊规则和法规体系与国家立法和/或欧洲指令相协调时出现的困难。例如,国际体育一直无法摆脱欧洲关于欧盟内部从业者自由流动的规定,以及体育联合会在与媒体的谈判中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的规定[24]。但是,国际奥委会认为体育应得到特殊考虑,因此一直致力于说服国际机构(联合国、欧盟、欧洲理事会)在国际条约中承认体育的特殊性(2000年的《尼斯宣言》,最重要的是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该条约第165条赋予欧盟明确的体育权限,并为欧洲形成共同的体育政策提供了基础)。这一努力相当成功,许多国际决议和欧洲指令现在都承认体育的社会和教育作用(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2007年关于体育的白皮书,欧洲议会2021年11月23日关于欧盟体育政策的决议)。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欧洲体育模式及其在教育、健康和社会包容等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的积极影响”(来自对体育专家的访谈)。这一战略催生了2个保护体育诚信的框架:2014年批准的欧洲委员会《操纵体育比赛公约》和2015年12月通过的国际奥委会《防止操纵比赛守则》。2017年,国际奥委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启动了“体育领域反腐败国际伙伴关系”,其目的是“将国际体育组织、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以加强和支持消除腐败的努力”。2009年,联合国大会授予国际奥委会观察员地位,使其能够直接为联合国计划作出贡献,并向各国政府宣传体育运动。然而,这些象征性和法律上的国际认可越来越明确地受到执行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政府机构或部门的限制,政府机构或部门要求国际和国家体育机构不断改善其组织治理[25]。这正是国家立法对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治理变得更具强制性的原因[26]。
1.3 组织治理
根据瑞士法律,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组织管理形式非常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最多有115名成员(2023年为99名现任成员),这些成员由现有成员增选产生。这些成员在国际奥委会的年度大会(即全会)上的主要权力是批准年度报告,选择奥运会(夏季、冬季和青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并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自1980年以来,国际奥委会由其主席与一个15名成员的执行委员会(相当于董事会,包括4名副主席)共同运营。另设有诸如运动员委员会、公共事务和企业传播委员会、奥林匹克项目委员会等32个委员会(截至2022年),这些委员会由专家和国际奥委会成员组成,就特定问题向全会、执行委员会和/或主席提供建议。
国际奥委会行政部门负责日常运营,自200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行政部门已经变得更加专业化,现在雇佣了近
1000 名长期员工[27]。其中约100名员工在位于马德里的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总部为奥林匹克网络电视频道(OCS)工作,该频道由国际奥委会于2016年建立,用于播放奥运会正赛及赛前各类比赛的档案录像。行政部门工资的大幅增加,特别是主管薪酬5 的增加,引发了关于它是否仍然物有所值的质疑。尽管国际奥委会承诺将总部运营成本控制在收入的10%以下,但实际比例似乎远高于此6 。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管理原则是,由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增选委员
7 管理该机构,其受薪管理人员实施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并通过年度活动和财务报告对结果进行监督,这些报告自2014年以来变得愈加详细和透明。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大洲联合会等则有着类似的治理结构。盐湖城2002年奥运会贿选丑闻的爆发是国际奥委会组织治理的转折点[28]。面对强烈的政治和媒体压力,国际奥委会的“制度性回应”[29]是基于特别召开的国际奥委会2000委员会(The IOC 2000 Commission)的建议,对其治理进行的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年龄限制从80岁降至70岁,并将其委员构成改为包括15名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15名国家(地区)奥委会主席和15名运动员,其中,运动员的委员任期最长为8年,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和国家奥委会主席的委员任期则随其主席任期结束而终止。新规则改变了国际奥委会成员的社会构成,使其变得更年轻化且吸纳了更多女性(2023年的99名委员中有38名是女性),并与国际体育世界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成员更替率高(45名成员的任期仅为8年)也使得国际奥委会主席更难控制该组织的成员资格。目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任期限制为8年,如果再次当选,任期为4年。改革举措还包括引入一个由道德委员会监督的道德准则。然而,该委员会并未积极主动地制裁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违规行为,例如国际足联的布拉特和阿维兰热、世界田联(原国际田联)的迪亚克,以及国际自行车联合会的韦尔布鲁根
8 [30]等著名的国际奥委会腐败成员为避免受到委员会的制裁,辞去了其委员职务。当托马斯·巴赫于2013年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国际奥委会面临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削弱国际奥委会的国际地位,并打破体育领域和奥林匹克运动内在的政治平衡。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托马斯·巴赫显示出“现实政治”大师的优势,根据各种情况调整自己的策略。
2. 托马斯·巴赫的“现实政治”风险管理方法
在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21年间(1980—2001年),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监督实施了一场奥运会革命,使奥运会远超顾拜旦的最初理念,转变为一个全球品牌[31]。2001年,雅克·罗格接替萨马兰奇成为主席时,国际奥委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涉及体育诚信和道德,以及体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展示国家软实力,特别是在金砖国家和海湾国家。至托马斯·巴赫(训练有素的律师和击剑奥运金牌得主)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奥林匹克主义正面临一场合法性危机。托马斯·巴赫采取了一种务实的现实政治方法来应对这场危机,而这一危机是由以下几个棘手问题共同造成的:
①西方国家的公众对举办奥运会,尤其是对举办冬奥会持怀疑态度(在1968—2022年期间,就是否申办冬奥会举行的31次全民公投中,有18次投了反对票,就夏季奥运会举行的几次全民公投也投了反对票)[32]。②保护体育诚信(兴奋剂、操纵比赛、国际体育领导人的腐败、精英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的斗争,以及奥林匹克世界应如何接纳“性少数群体运动员”等新问题。③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如何应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及其对体育的利用(国家支持的兴奋剂滥用、2022年俄乌冲突、普京宣布俄罗斯将主办2024年金砖国家运动会,该运动会希望吸引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至少70个国家参加)[33]。④对大型体育赛事影响气候和缺乏环境可持续性的批评。⑤来自新形式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体育运动(如电竞、综合格斗、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生存运动)的竞争。⑥Z世代(1997—2010年出生的人)和Alpha世代(2010年以后出生的人)的行为特点是习惯于使用虚拟平台和不太活跃的生活方式,这可能预示着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34]。这些年轻一代的体育消费方式截然不同:凯捷研究院2023年的《全新的球类运动》报告[35]显示,77%的Z世代受访者和75%的Y世代(1980—1995年出生的人)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喜欢在体育场馆外观看体育比赛,而70岁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 32%。
托马斯·巴赫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方法主要是风险管理,其基础是评估国际奥委会何时以及对谁可以采取强硬立场,何时需要采取更具和解性的方法。他基于2个主要前提——“通过善治实现负责任的自治”和“体育和奥林匹克主义造福社会”维护国际奥委会的立场,然而,这2个前提都值得商榷。
2.1 通过善治实现负责任的自治
托马斯·巴赫在2013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不久,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了“通过善治实现负责任自治”的表述。次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体育独立和自治以及国际奥委会领导奥林匹克运动的决议。在此,自治意味着体育组织有权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并免受政府和其他外部行为者(包括私人资助者、赞助商、广播公司)的干涉,如《奥林匹克宪章》第5条所述:“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组织应保持政治中立。它们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自由制定和控制体育规则,决定其组织的结构和管理,享有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选举权,并有责任确保善治原则得到贯彻。”
自治这一概念在民主国家可能具有意义和价值,但在不具备言论自由或严格限制言论的国家,要适用自治原则,虽并非不可能,但更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或直接(领导人由国家任命和/或是在职政治家)或间接(领导人受政府控制)受到政治控制[36]。一些国家(地区)奥委会由该国总统(如阿塞拜疆、海湾国家)或体育部长领导。
托马斯·巴赫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国际奥委会在3项新的治理和管理原则中体现了“负责任的自治”理念:宣布清晰的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战略路线;巩固商业模式;基于提高透明度、效率和社会责任的全球化精神,更好地监督和报告其行动[5]。托马斯·巴赫的施政“围绕着非常强大的主席权力进行了非常集中的管理”(来自对学者的访谈),以恢复宣布改革时所寻求的“信誉”(《奥林匹克2020议程》)。
托马斯·巴赫在2份战略路线图——2014年发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40项战略建议)和2021年发布的《奥林匹克2020+5议程》(15项建议)中阐述了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发展的愿景。国际奥委会声称已落实了2014—2021年40项建议中的88%。然而,国际奥委会依靠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来实施其建议,“并非所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都有资源来有效实施这些建议”(来自对学者的访谈)。
托马斯·巴赫和他的团队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巩固国际奥委会的商业模式,确保将其收入中更大比例的份额“均衡”地重新分配给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奥组委、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托马斯·巴赫担心的是,国际奥委会60%的收入仍然依赖奥运会转播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因为美国电视网为转播权支付了大笔费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为2020—2032这一周期支付了76.5亿美元。 此外,国际奥委会2/3的顶级赞助商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公司,因此,尽管当今世界多极化,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国际奥委会80%的收入来自西方世界。虽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转播权有所增加,但与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合同相比仍微不足道。例如,澳大利亚媒体集团Nine Entertainment仅为 2024—2032周期支付了1.91亿美元,尽管这一周期包含了在澳大利亚本土举办的布里斯班2032年奥运会。奥运商业专家帕特里克·纳利(Patrick Nally)[37]认为这一数额 “低得惊人”,并敦促国际奥委会“重塑”其“老化”的商业模式。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收入,可以花费近2亿美元在洛桑新建一个总部,并于2019年投入使用。
在观众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在继续依赖美国资金和NBC转播权合同的同时,还试图确保奥运会的地缘政治地位,从而逐步巩固其商业模式。托马斯·巴赫在这方面的第一批举措旨在保护奥运会的声誉,一些学者认为奥运会声誉受到以下两方面的损害:将赛事举办权授予威权政权的争议(如索契2014年冬奥会[38]);政治问题和/或腐败制裁(如里约2016年奥运会和东京2020奥运会)已经玷污了奥运会的声誉,这也影响了最近的足球世界杯赛(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赛、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赛)。不同的是,国际足联继续将其旗舰比赛举办权授予威权主义国家(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赛、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赛、2034年沙特阿拉伯足球世界杯赛),而国际奥委会已将所有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授予西方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运会候选城市数量的缺乏使国际奥委会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因为在2017年,国际奥委会历史上首次在一届全会上将两届夏季奥运会分别授予巴黎(2024年奥运会)和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此举是新“双赢(国际奥委会和候选城市)”理念的一部分,旨在避免Andreff[39]所提及的“中标诅咒”
9 。基于同样的原因,以及将奥运会授予另一个西方国家的契机,国际奥委会提前多年10 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而没有邀请其他国家申办。冬奥会举办权的授予也遵循类似轨迹——继科尔蒂纳丹佩佐通过竞选获得2026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后,国际奥委会将2030年和2034年的举办权授予了各自的唯一候选城市——法国的阿尔卑斯、美国的盐湖城。对于国际奥委会的西方利益相关者而言,聚焦西方(尊重人权和申办质量、利用现有设施减少赛事对环境的影响)是令人放心的,但考虑到中国、印度、“薄荷四国”(MINT Countries——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以及海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人口方面的崛起,这种倾向就值得商榷了。除了战略路线图和业务模式这两块基石之外,托马斯·巴赫任期内的国际奥委会还展现出以提高透明度、加强性别平等和改进控制机制为中心的新治理原则。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瑞士,而瑞士保留着保密文化,因此国际奥委会没有义务公布其账目。尽管如此,自2014年以来,国际奥委会通过官网公布其年度报告、向奥林匹克运动各成员机构重新拨款的金额,以及国际奥委会委员所获津贴和日薪金额。例如,这些数字表明,支付给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各委员会主席的报酬仍然是合理的,与支付给大型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薪金相一致(国际足联或国际奥委会支付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并非如此)。国际奥委会的改革在性别领域取得的进展最大,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将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性别均等(在东京举行的第32届夏奥会中的女性运动员占比接近50%,该届奥运会设有18个男女混合小项)。官员(法官/裁判员)和国际奥委会内部的性别均等也取得了进展,2013—2020年,国际奥委会女性成员增加50%,国际奥委会委员中的女性人数增加了100%(2020年,女性占委员的48%)。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各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实现性别均等方面的进展变化更大但往往令人失望。在40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只有2位女性主席,只有10%的国家(地区)奥委会由女性领导[40]。早在2008年,国际奥委会即已宣布其目标是到2030年至少有30%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拥有女性主席,“但如果不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采取强制措施,并像许多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做的那样实行性别配额,这将很难实现”(来自对专家的访谈)。
实现善治的举措还包括采用新的机制。2008年,国际奥委会制定了《奥林匹克运动内部善治的基本通用原则》,并随后将其纳入道德准则。根据《奥林匹克宪章》,所有奥林匹克运动内的组织都应适用这些原则,但“很少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这样做”(来自对体育组织高管的访谈)。此外,尽管国际奥委会在2014年设立了道德与监察办公室,以确保各组织遵守这些原则,但在支持这些原则的实施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1 。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严格执行这种普遍主义治理规范并不一定切实可行,因此它们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愿望而非实际结果”[41]。基于对伊朗国家奥委会如何应用国际奥委会治理原则的研究[42]发现,这些规范应该允许国家、地区和地方行为体根据其价值观和优先事项选择、修改和权衡“良好”治理的指标和操作措施。事实上,治理是一个规范性概念,“相对于所期望的目标,建立在来自国家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之上,反映了不同的全球本体论”,这使得考虑文化因素变得更加重要[42]。
在2015年国际足联贪腐丑闻之后,国际奥委会开始倡议和鼓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使用奥运会夏季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的治理评估工具,即一份自我报告治理问卷,包含50项指标,分为5个领域(透明度、诚信、民主、体育发展与团结、控制机制)[43]。欧洲委员会2018年的Jensen Report对这一倡议表示欢迎,表示该倡议的成果已在4个年度(2017年、2018年、2020年、2022年)发表,但报告也批评了其缺乏独立性,并主张制定一个关于体育治理的ISO标准。此外,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的管理质量仍然参差不齐。例如,2023年6月22日,由于国际拳击联合会(IBA)持续的治理失策,国际奥委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撤销了对该联合会的承认。在2019年被暂停资格并因多次裁判丑闻而名誉扫地后,国际拳击联合会目前已经彻底失去了本可从国际奥委会获得的资金以及在巴黎和洛杉矶奥运会上组织比赛的权利(尽管这项运动仍在奥运会项目中)。因此,它将不得不依赖其他资金来源来偿还其巨额债务。
2.2 彰显体育积极影响以应对质疑
奥运会的短期影响和长期遗产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44],他们经常质疑奥运会对旅游业、体育参与、社会(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社会凝聚力的提高等)以及地区市场营销的积极影响[45]。鉴于其目标是“通过体育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国际奥委会2014年年度报告),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并展示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积极影响。国际奥委会通过体育和奥运会影响社会的主张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可持续性、通过体育促进发展、奥运会的积极遗产。
2015年,联合国承认体育对推进其2015—2030年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国际奥委会随后将其作为2016年推出的环境政策的框架。这项政策要求国际奥委会在性别平等、人权和(环境)可持续性等3个领域以及作为国际体育组织、奥运会的所有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等3个层面采取行动。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国际奥委会在其组织内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过程中取得的进展远远超过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他方面。人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际奥委会目前仍在制定自己的举措,并由其行政部门内设立的一个特别小组(2021年成立)提供咨询。除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降低举办奥运会的成本外,国际奥委会2021—2024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侧重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循环经济。在气候行动方面,它采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为各国设定的目标,并承诺到2030年将其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减少50%。然而,国际奥委会将通过碳中和实现大部分减排,只有相对较小的贡献来自减少与其总部运营和奥运会相关的排放。此外,国际奥委会与少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签署了联合国体育促进气候行动倡议,该倡议是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1)之后发起的。
除了国际奥委会在全世界推广但各奥组委、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难以付诸行动的环保举措[46],奥林匹克运动还必须展示体育对教育、健康、发展以及在人口非常年轻且迅速增长的国家(印度、非洲及东南亚国家)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2021年推出的“奥林匹克主义365”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加强体育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在世界和平与国际团结领域,国际奥委会于2015年成立了难民奥林匹克队,以提高人们对目前2 000万难民的认知,难民奥林匹克队在里约2016年奥运会上首次参赛。
有一种奥运会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主办奥运会大大加快了东道国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如巴黎2024年奥运会之前塞纳-圣但尼地区和伦敦2012年奥运会之前东伦敦地区的建设[47],然而,有学者[47]批评这会造成贫民窟效应和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确保奥运会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对各奥组委而言也非常重要,其设立了专门的部门来规划这方面的工作。国际奥委会也通过研究和相关工具来反驳诋毁者 [48],并在2021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奥运场馆的125年:奥运会后的使用》),该报告声称在21世纪举办的奥运会的永久性奥运场馆中有92%仍在使用,所有奥运设施中有85%仍在使用。
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努力改变其形象并改善奥林匹克运动的治理和管理实践,但也涉及招致质疑或攻击的权衡和妥协。换言之,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在其目标和主要利益相关者接受变革的能力和意愿之间进行平衡。
3. 讨论:一种制度平衡的艺术
托马斯·巴赫的现实政治方法旨在保护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性,而新制度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是一个部门内部如何发生变革的,两者之间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合法性是制度方法的核心。机构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运作符合所在系统的规范、信仰及规则的程度。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认识到,机构是在多机构环境中运转的,其主要目标是生存。这就需要在机构环境中建立一定的合法性。
3.1 制度工作与合法性
首先,国际奥委会是体育和奥林匹克体系的主要“机构企业家”(Dimaggio1988年定义),因为正是国际奥委会实施了机构变革,才能实现其目标。但是,实现战略目标是一个集体过程,国际奥委会必须让其他参与者参与其中并建立有益的互动关系。托马斯·巴赫的战略包括开展新制度理论所说的“制度化运作”[49],根据具体情况创建、维护甚至颠覆制度。制度化运作的概念阐明了国际奥委会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的实施用以确保公共及私人商业组织规范,影响体育运动[50],使其符合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
唯一获得可接受安排和妥协的方法是通过这种集体过程,在基于伙伴关系的系统治理形式的框架内,通过承诺善治或更好的组织治理实现更和谐的政治关系。这一框架也使国际奥委会能够适应或赢得机构的支持,从而维持其政策、获得资源并最终确保其合法性。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组织通过表明其符合标准、规则、信仰,以及认知与道德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这些模式提供了指导人类行为和构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意义系统。换言之,合法性不是来自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51]以及社会规范的遵从,而主要基于组织间的共谋[52]。
理性指导行动符合既定规则(“嵌入式代理”[53]),而反思性指个人辨别、想象和改变这些规则的能力,以及超越制度(国家、社会团体等)限制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国际奥委会通过向主办国实施《奥林匹克宪章》并在奥运会期间进行各种法律和财政优惠条件的谈判,实现了这一举措。
评估组织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根据Suchman[54]和Deephouse等 [55]的观点,这涉及分析3种类型的标准:认知、社会政治、道德。当社会实践与现有模式差异过大且难以理解时,就很有可能遭到排斥。例如,如果某届奥运会(如索契2014年冬奥会)被认为对环境造成过大影响(代表团和游客的旅行、大量场馆建设等)[56],就会导致认知合法性的缺失(特别是对西方观众而言)。社会政治合法性源于组织在其环境中获得有影响力的机构的支持和认可。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政治合法性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国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补贴)和国际机构的认可(如被欧盟指定为“欧洲体育模式”的担保人并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地位)。反之,这种社会政治合法性也使奥林匹克运动能够获得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资金、人员、形象、社会地位、公众舆论等)。道德合法性则在于社会认为某种实践或组织形式符合现有的文化规范。奥林匹克运动的道德合法性来自奥林匹克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体育运动的所谓积极影响,尽管现在许多精英运动员和科学研究都对这些影响提出了质疑。事实上,竞技体育并不会自动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是否产生效益取决于开展的方式和场景。例如,创造优异成绩对精英运动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无论是在运动生涯期间还是之后)。对奥林匹克运动道德合法性的其他威胁还包括许多体育组织未能任命女性担任高级职位。
正如Maguire等[57]所指出的,合法性会受到攻击,这些攻击可能会导致曾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组织实践和形式的去制度化和消失。此类实践包括:①体育高管在公共管理、商业和体育领域身兼数职,将引发孤立、利益冲突,甚至腐败[58];②在自然降雪不足且设施不完善的地区举办冬季奥运会;③为了建造奥运设施而驱赶无家可归者;④期望经济状况岌岌可危的运动员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参加奥运会。如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并确保国际奥委会回应世界的重大挑战,更加顺应社会变化,将可能导致奥运会的消亡。
3.2 对制度进程的战略回应
对于具有社会目标的组织而言,获得合法性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国际奥委会这样的机构必须“实施、操控并利用引人共鸣的象征符号以获得社会支持”[59]。Oliver[51]列出了组织用来减轻制度压力并克服危机的战略反应和相关策略的类型,这些战略旨在从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中提取最大化利益。他们的策略通常是通过化解外部压力(媒体、法律、政治等)来平息冲突和/或危机。
这5种战略——顺从(acquiescence)、妥协(compromise)、规避(avoidance)、反抗(defiance)、操控(manipulation)的目的不是改善绩效,而是保持形象并赋予组织合法性。国际奥委会在3个不同层面使用以上5项战略:体育/奥林匹克体系层面、组织间层面(国际奥委会与欧盟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以及组织内层面(国际奥委会的运作)。如表2所示,国际奥委会经常在奥林匹克体系层面使用妥协和操纵战略。规避等其他战略可能导致脱钩,即国际奥委会的言辞与其行动脱节。一些组织可以利用这些做法作为保护机制,而不会受到质疑,但国际奥委会的情况并非如此,它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并可能受到非政府组织、调查记者和国家司法部门的攻击。
表 2 根据1991年版Oliver框架改编的制度进程战略对策Table 2.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dapted from Oliver's framework (1991)战略 对策 举例 应用 默许 适应 适应无形的规范,并将其视为既定规范 社会变革(性别平等、残障与失能人士保障、多样性等) 模仿 模仿机构模式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跨国公司采用的道德合规做法 遵守 遵守规则,接受规范 托马斯·巴赫的口号:“要么改变,要么被改变”;接受欧洲法律,但要求承认体育的特殊性(动员政治支持) 妥协 平衡 平衡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将奥林匹克收入重新分配给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再分配比例) 安抚 安抚机构利益相关者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奥林匹克休战;国际体育仲裁院(比国家法院更快、更谨慎、更有效地解决法律纠纷)让各国政府参与反兴奋剂斗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协商 与机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 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政府(适用“奥林匹克法规”) 规避 隐藏 与规则等不适合 不适用“善治的普遍原则”(2009)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善治措施(奥运会夏季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2016) 缓冲 放松机构限制 接受媒体/财务要求(NBC规定的奥运会某些项目的时间安排,例如东京2020奥运会的游泳项目);拒绝补偿运动员,但放松对个人形象权的规定 逃避 更改目标、活动或领域 国家司法系统(通过创建体育司法和自律系统——内部道德委员会来实现“家丑不外扬”) 忽视 忽略 无视规范和明确的价值观 公众舆论和非政府组织(关涉人权和可持续性,依靠奥运会与残奥会东道主) 挑战 废止惯例和指令 以体育自主和政治中立的名义谴责某些形式的政治干预(但接受其他形式的干预) 攻击 攻击机构压力的来源 操纵解散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2017年)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2022年)——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伞式机构和国际奥委会的历史性制衡机构 操纵 合作 纳入有影响力的机构 新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外部游说/内部地缘政治平衡)和新的奥林匹克运动(吸引年轻人和新市场,特别是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国际检测机构(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 影响 影响价值观和标准 与奥运会起源和顾拜旦复兴奥运会有关的神话;围绕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普遍性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 控制 主导社会和机构流程的各个方面 奥林匹克宪章(宪法框架);将奥林匹克品牌定位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奥林匹克2020+5议程》(奥林匹克运动战略发展路线图) 这种新制度理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阐明了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根据危机的性质和所涉利益采取的主动和被动战略,以对抗试图通过制度压力施加外部监管的尝试,并避免由于社会变化而出现的非制度化。战略回应取决于制度压力的性质、施压方式、发生的时间(危机或稳定),以及战略部署的层面(宏观—中观—微观)。国际奥委会传递的国际合法性信息概括如下:政治机构、商界和整个社会都需要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奥运会和残奥会。因此,它们需要国际奥委会,即使这些机构不完美(正如政治和商业世界一样)。体育领域正在尽最大努力改进,即使当前改进的规模尚小。奥林匹克主义和体育对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教育、社会融合和健康等众多领域具有积极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建立在民主、非营利原则和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因此,奥林匹克主义是社会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完全私有化的体育或完全由国家控制的体育都不符合社会利益:前者可能会使许多人被排除在体育之外;后者则需要大量公共投资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体育。
这一历史上构建的信仰和意义系统由托马斯·巴赫及其公关传播团队持续推广,迄今已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分别在国际和国内推广这一信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特别努力地游说将其植入欧盟体系。这些努力使国际奥委会得以在许多领域保持其自我监管的权利。
国际奥委会利用其话语(自2014年以来发表的演讲和发布的众多文件),以及在善治、可持续性和完整性等问题上的脱钩实践,围绕国际奥委会主导的奥林匹克体系监管新形式建立起一种社会意义。它试图统一奥林匹克组织领域的实践
12 [60],尽管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将其意志强加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地区)奥委会,这些机构在其运作和专业化方面仍非常多样化。此外,以尊重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地区)奥委会的自主权为名,“国际奥委会拒绝参与它们的治理和运作”(来自对专家的访谈)。相反,国际奥委会依赖于制度同构[61]以聚合和统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会,甚至各奥组委的行为。以下3种制度同构性的类型[61]都可以在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体系核心组织的行动中看到:①规范同构。国际奥委会收入的重新分配,以及各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专家网络(通过专业体育经理人协会得到加强)之间的人员流动,提高专业化程度,从而实现规范同构
13 。专业化也由专门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管理的培训机构推动,这些机构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经常从这些项目中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国际奥林匹克学院(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国际体育科学与技术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S)14 和体育组织管理高级管理硕士(Executive Masters in Sport Organisations Management, MEMOS)15 提供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奥林匹克运动管理硕士学位课程16 。②模仿同构(复制善治、可持续性和诚信的实践)。奥林匹克组织可能会模仿其他奥林匹克组织、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难民等问题的框架)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跨国合作伙伴(如符合道德规范)的做法。③强制同构。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宪章》和奥林匹克收入再分配标准施加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压力。面对奥林匹克组织在专业化方面的巨大异质性,国际奥委会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应对出现的问题、不一致性和危机。它的战略根据政治现实作出调整,有时也会避开敏感的国际问题,让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己作出决定。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国家支持的兴奋剂滥用问题采取了这种做法(允许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行制定里约奥运会后俄罗斯运动员重返赛场的标准);在跨性别运动员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国际奥委会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在特定条件下参赛,但赋予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其项目的否决权。世界田径联合会是唯一使用过否决权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然而,这种方法导致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采取不同立场,奥林匹克运动无法以统一的声音发声,加剧了其不一致性。例如,2023年,国际击剑联合会在世界锦标赛上因乌克兰运动员拒绝与俄罗斯运动员握手而取消了其资格。国际奥委会则立即呼吁该联合会撤销这一处罚,允许这名运动员参加2024年奥运会。2023年夏季,乌克兰放松了其立场,不再要求乌克兰运动员抵制所有有俄罗斯运动员参加的比赛。
正因为如此,国际奥委会的制度化运作可以说是一种平衡行为,它必须处理奥林匹克等教育和人文运动所面临的众多伦理困境所产生的悖论和矛盾:商业与奥林匹克价值观“纯洁性”之间的矛盾、精英体育表现与竞赛诚信及运动员健康之间的矛盾、领导人的模范作用与利益冲突和腐败之间的矛盾、体育的政治中立性与地缘政治工具化之间的矛盾、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奥林匹克人文主义与专制政权举办奥运会之间的矛盾······
Hardy等[61]指出,组织领域可能存在3种状态:新兴、稳定成熟和危机中的成熟。在危机中的成熟领域,如奥林匹克主义,充满了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实践和形式的挑战预示着可能的衰落和去制度化进程,随后是制度创新和再制度化[62]。利用制度企业家行动(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来巩固其领导地位会使国际奥委会受到批评,并增加其遵守社会规范的压力,从而限制其自由行动的能力。因此,国际奥委会倾向于对社会变化作出反应,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引领社会变革。
其他类型的社会评价,尤其是组织的地位(在组织等级中的位置)、声誉(服务/产品的质量指标),以及是否被污名化或受到公众的反对[63],也会对组织的合法性产生影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正面和负面的社会评价是否会影响组织的绩效,以及它们是否与其社会责任[5]和可持续发展[64]战略相关联并保持一致。Ben Slimane等[65]从战略管理角度出发,结合基于资源的观点(建立竞争优势所需的关键资源/能力)和制度工作的概念,制定了一个框架。该框架展示了某一领域的行动者如何利用4种关键的机构能力(理解环境、构建合理性和实现合理化、动员政治支持、动员物质资源)来开发资源和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对于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国际奥委会就会发现,国际奥委会捍卫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是确保其经济效益。
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国际奥委会机构及制度化工作的主要目标——要保持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现有地位,以及个别参与者(领导人、负责人等)的现有地位;还是要赋予机构和奥林匹克运动新的社会地位(“愿景”)?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体育政策的未来,还涉及体育在社会中的作用,为此,体育界应让其主要合作伙伴参与其中。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展示新制度方法的旨趣以及在危机领域(如奥林匹克主义)开展的合法化工作。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托马斯·巴赫自2013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带领其团队为减轻国际奥委会的机构压力以及克服各类危机而采取的策略。国际奥委会在过去10年中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市场营销、奥运项目、性别平等、专业化和透明度方面。然而,许多观察家仍然怀疑这些变化的可信度。托马斯·巴赫2014年的口号“改变或被改变”,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仍然适用。“不确定性”体现在2022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数字化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等方面。国际奥委会决定建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在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时被排除在国际比赛之外)在特定条件下重返赛场,这一决定令希望国际奥委会采取更强硬立场的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但这也体现了国际奥委会为避免与强大的参与者对抗而作出的妥协
17 。国际奥委会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协调其言论、实践和成果,以及如何在一个由政治博弈主导的体系中寻求(地缘)政治平衡。奥林匹克大家庭仍然经常在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66]所描述的“礼物与回礼”系统中运作,在该系统中,“给予—接受—再给予”的义务造成了领导者之间的依赖关系[58]。现实情况是,尽管出现了一些制衡力量(如瑞士政府
18 、非政府组织19 和旨在“帮助运动员在世界体育运动中获得更多发言权”的“全球运动员”组织等),但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权力面前,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仍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制衡力量。正视并接受独立外部评估的必要性、为投诉者提供更好的保护[67],以及在授予奥运会举办权和起草主办城市合同时更加重视人权[68],是提高国际奥委会、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关键。声明 本文英文版2024年2月以优先数字出版的形式首发于Sport in Society杂志[69],埃玛纽埃尔·贝叶教授持有版权并授权易剑东(本文通信作者)、徐笑菡(本文第三作者)翻译后投稿本刊。
作者贡献声明:埃玛纽埃尔·贝叶:提出论文选题,撰写、修改论文;作者贡献声明:易剑东:校对、审核论文;作者贡献声明:徐笑菡:翻译论文。1 ① 根据欧洲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欧洲体育宪章》,体育诚信包括个人诚信、竞技诚信、组织诚信。2 ② 国际体育攀岩联合会,2007 年成立。3 ③ 国际奥委会将滑板列入奥运会项目,将这项运动纳入国际轮滑联合会(2017年更名为世界轮滑总会),该联合会管理其他轮滑项目,包括花样轮滑、速度轮滑、轮滑曲棍球和直排轮滑曲棍球。然而,只有最初作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滑板运动将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4 ① Zwift(自行车)、Just Dance(舞蹈)、Gran Turismo(赛车)、Virtual Regatta(帆船)、国际象棋、WBSC eBaseball: Power Pros(棒球)、Virtual Taekwondo(跆拳道)、Tennis Clash(网球)、Fortnite(射击)、Tic Tac Bow(射箭)。5 ① 某重要非政府组织批评了国际奥委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总干事级别薪酬为142.6万美元,首席运营官级别薪酬为92万美元,详见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41368/david-owen-blog-us-document-ioc-finances。6 ② Patrick Nally是奥林匹克业务方面的专家,他估计该比例高达30%,但没有明确引用来源。他还质疑当前10%的比例是尚未融合营销公司TMS(国际奥委会100%拥有的商业公司,负责管理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和营销合同)、国际奥委会拥有的OBS以及奥运会相关成本的数据。7 ③ 委员每年获得6500 欧元的行政开支和418欧元的日常工作费用。国际奥委会主席每年领取22.5万欧元(资料来源:《国际奥委会2023年度报告》)。8 ④ 对国际体育道德准则和道德委员会的批判性分析,见参考文献[30]。9 ① 在申办一届奥运会的过程中,候选城市会低估基础设施建设和举办赛事的成本,从而夸大自己的实力。对于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而言,这种低估导致实际成本大幅增加,可能是最初公布的两倍。10 ② 提前11年(而非通常的7年)授予主办权。11 ③ 2016年欧洲奥委会设计了一个名为 SIGGS(国家/地区奥委会善治自我评估工具)的治理学习和评估工具,详见https://www.siggs.eu/index.html。12 ① Dimaggio和Powell将组织领域定义为属于制度生活同一“领域”的一组组织。即在这一领域中,各组织相互承认,具有相同的现实感和认知模式,并围绕制度化的实践和形式进行互动。因此,一个组织领域包括所有帮助该领域建立和维持制度的参与者。13 ① 例如,瑞士体育经理人协会就在瑞士发挥了这一作用。14 ② 位于瑞士洛桑的知名体育管理学院。它成立于2000年,由国际奥委会、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洛桑大学(UNIL)和其他几家主要的学术和体育机构共同创办。15 ③ 专为体育管理专业人士设计的国际硕士学位项目。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利用该硕士学位培训奥林匹克运动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16 ④ 国际足联联合国际体育研究中心(CIES)和欧足联学院为足球相关人士提供“内部”培训课程。17 ①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https://www.swissinfo.ch/fre/economie/-le-cio-est-sous-pression- des-occidentaux-/48619246。18 ② 2014年12月12日,瑞士议会通过了一项打击洗钱的法案。该法案的标题“Lex FIFA”很好地说明了其目标。据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国际奥委会市场部工作的罗兰·比歇尔(Roland Büchel)称,“瑞士议会和人民已经受够了腐败”(《世界报》,2014年12月11日)。19 ③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国际足联丑闻的框架内发起运动,要求监督国际足联领导人的诚信,保护举报人(就像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并要求进行独立监督以促进其组织改革。 -
表 1 重新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大致金额(现金和实物)[16]
Table 1 Approximate amounts redistributed to NOCs and Olympic IFs (cash and benefits in kind)
亿美元 在此时间节点后重新分配 国家(地区)奥委会 奥林匹克项目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 3.01 2.97 伦敦2012年奥运会 5.20 5.20 里约热内卢2016年奥运会 5.40 5.40 东京2020奥运会 5.40 5.40 图灵2006年冬奥会 1.36 1.28 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 2.15 2.09 索契2014年冬奥会 1.99 1.99 平昌2018年冬奥会 2.15 2.15 表 2 根据1991年版Oliver框架改编的制度进程战略对策
Table 2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dapted from Oliver's framework (1991)
战略 对策 举例 应用 默许 适应 适应无形的规范,并将其视为既定规范 社会变革(性别平等、残障与失能人士保障、多样性等) 模仿 模仿机构模式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跨国公司采用的道德合规做法 遵守 遵守规则,接受规范 托马斯·巴赫的口号:“要么改变,要么被改变”;接受欧洲法律,但要求承认体育的特殊性(动员政治支持) 妥协 平衡 平衡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将奥林匹克收入重新分配给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再分配比例) 安抚 安抚机构利益相关者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奥林匹克休战;国际体育仲裁院(比国家法院更快、更谨慎、更有效地解决法律纠纷)让各国政府参与反兴奋剂斗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协商 与机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 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政府(适用“奥林匹克法规”) 规避 隐藏 与规则等不适合 不适用“善治的普遍原则”(2009)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善治措施(奥运会夏季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2016) 缓冲 放松机构限制 接受媒体/财务要求(NBC规定的奥运会某些项目的时间安排,例如东京2020奥运会的游泳项目);拒绝补偿运动员,但放松对个人形象权的规定 逃避 更改目标、活动或领域 国家司法系统(通过创建体育司法和自律系统——内部道德委员会来实现“家丑不外扬”) 忽视 忽略 无视规范和明确的价值观 公众舆论和非政府组织(关涉人权和可持续性,依靠奥运会与残奥会东道主) 挑战 废止惯例和指令 以体育自主和政治中立的名义谴责某些形式的政治干预(但接受其他形式的干预) 攻击 攻击机构压力的来源 操纵解散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2017年)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2022年)——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伞式机构和国际奥委会的历史性制衡机构 操纵 合作 纳入有影响力的机构 新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外部游说/内部地缘政治平衡)和新的奥林匹克运动(吸引年轻人和新市场,特别是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国际检测机构(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 影响 影响价值观和标准 与奥运会起源和顾拜旦复兴奥运会有关的神话;围绕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普遍性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 控制 主导社会和机构流程的各个方面 奥林匹克宪章(宪法框架);将奥林匹克品牌定位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奥林匹克2020+5议程》(奥林匹克运动战略发展路线图) -
[1] CLASTRES P. Inventing an elite:Pierre de Coubertin and "sporting chivalry"[J]. French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2005,22(2):51-71
[2] CHAPPELET J L. Le système olympique [M]. Grenoble:Presses Universitaires,1991:254-260
[3] CHAPPELET J L. Olympic Games:Rekindling the flame[M]. Lausanne:EPFL Press,2016:13-14
[4] HUBERMAN A M,MILES M B.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companion[M]. Thousand Oaks,CA:SAGE,2002:171-196
[5] ASOIF. Future of global sport [EB/OL]. [2024-05-15]. https://www.asoif.com/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future_ of_global_sport.pdf
[6] ASOIF. Reports and documents published by ASOIF's Governance Task Force and Governance Support and Monitoring Unit (GSMU)2017–2022 [EB/OL]. [2024-05-15] . https://www.asoif.com/governance
[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Global corruption report:Sport(2016)[EB/OL]. [2024-05-15].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publications/global-corruption-report-sport
[8] GEERAERT A. When sport meets business:Capabilities,challenges,critiques[M].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186-200
[9] WEINREICH J. How federations share the revenues from the Olympic Games [EB/OL]. [2024-05-15]. https://www.playthegame.org/news/how-federations-share-the-revenues- from-the-olympic-games/
[10] JEDLICKA S R. Sport governance as global governance: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por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2018,10(2):287-304 doi: 10.1080/19406940.2017.1406974
[11] ANASTASIADIS S,SPENCE L J. An Olympic-sized challenge: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pathology on maintaining and repairing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n sports governing bodies[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20,31(1):24-41 doi: 10.1111/1467-8551.12345
[12] HENRY I,LEE P C. The business of sport management[M]. London:Pearson Education,2004:25-41
[13] BAYLE E. Olympic social responsibility:A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M]// BAYLE E,CHAPPELET J L. From Olympic administration to Olympic governance. London:Routledge,2017:16-30
[14] HOYE R,CUSKELLY G. Sport governance[M]. London:Routledge,2007:1-31
[15]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2018. [R/OL]. [2024-05-15]. https://stillmed.olympics.com/media/Document%20Library/OlympicOrg/IOC/Who-We-Are/Commissions/Olympic-Solidarity/2018-Report/2018-OS-Annual-Report.pdf#_ga=2.254987456.978379868.1683192087-594927581.1678187184
[16] CHAPPELET J L. La communauté olympique. Gouvernance d'un commun socioculturel global[M]. 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2023:172
[17] BURKE P. Bach announces IOC plan to launch inaugural Olympic Esports Games[EB/OL]. [2024-05-15]. 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41738/ioc-to-launch-olympic-esports-games
[18] BERKELEY,G. ASOIF President claims IOC has become 'umbrella of sports movement' in backing of GAISF dissolution[EB/OL]. [2024-05-15]. 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30988/bitti-ioc-umbrella-sports-movement
[19] RYALL E,COOPER J,ELLIS L. Dispute resolution,legal reasoning and good governance:Learning lessons from appeals on selection in sport[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2020,20(5):560-576 doi: 10.1080/16184742.2019.1636400
[20] CHAPPELET J L,VAN LUIJK N. Th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global hybrid bodies:The case of 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M]//SAVIGNON A B, GNAN L, HINNA A, et al.Hybridity in the governance and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Leeds: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2018:167-191
[21] OHL F,FINCOEUR B,SCHOCH L. Fight against doping as a social performance:The case of the 2015–2016 Russian anti-doping crisis[J]. Cultural Sociology,2021,15(3):386-408 doi: 10.1177/1749975520977345
[22] ALTUKHOV S,NAURIGHT J. The new sporting Cold War:Implications of the Russian doping alleg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port[M]//NAURIGHT J,ZIPP S. Global markets and global impact of sports. London:Routledge,2020:36-52
[23] IOC. Safe sport[EB/OL]. [2024-07-25]. https://olympics.com/ioc/safe-sport
[24] WEATHERHILL S. Fair play please!: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C law to sport[J].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2003,40(1):51-93
[25] GEERAERT A,DRIESKENS E. Normative market Europe:The EU as a force for good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governance?[J].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2017,39(1):79-94 doi: 10.1080/07036337.2016.1256395
[26] DE DYCKER S.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Comparative law aspects[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2019,19(1):116-128
[27] CHAPPELET J L.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dministration[J]. Journal of Olympic Studies,2022,3(2):66-90 doi: 10.5406/26396025.3.2.05
[28] CHAPPELET J L. Une commission d'éthique pourla gouvernance du mouvement olympique[J/OL].[2024-05-15]. Éthique publique,2005,7(2):132-143.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thiquepublique/1947
[29] RAYNER H. Dynamics of scandal: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Clearstream[M]. Paris:The Blue Rider,2007:133-139
[30] CONSTANDT B,WILLEM A. Stimulating ethical behaviour and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The (non) sense of codes of ethics[M]//GEERAERT A, VAN EEKEREN F.Good governance in sport. London:Routledge,2021:210-220
[31] MILLER D. The Olympic revolution[J]. Paris,Payot & Rivages,1993:128
[32] CHAPPELET J L. Winter Olympic referendums:Reasons for opposition to the Games[M]//DICHTER H L, TEETZEL S.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at 100. London:Routledge,2023:210-225
[33] SANKAR V. Putin "Welcomes" Bloc Members to BRICS in 2024 Games [EB/OL]. [2024-05-15]. 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40156/putin-invites-brics-games
[34] WHO. Physical activity[EB/OL]. [2024-05-15].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physical-activity
[35] Capgemini Research Institute. A whole new ball game[R/OL]. [2024-05-15]. https://www.capgemini.com/insights/research-library/the-future-of-sports/
[36] GARCÍA B,MEIER H E. The "autonom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Assessing the fate of sports governance transplants in the Global South[J].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2022,4:972717 doi: 10.3389/fspor.2022.972717
[37] NALLY P. I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eading for its own titanic disaster? [EB/OL]. [2024-07-25]. 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41743/patrick-nally-big-read-ioc-financial
[38] ROSS M I,ARKIN Z,HUI F,et al. Critical commentary:A call to boycott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establish minimum human rights standards for Olympic hosts[J]. Journal of Emerging Sport Studies,2021(6):2-15
[39] ANDREFF W. Why is the cost of the Olympic Games always underestimated? The "curse of the auction winner"[J]. Papeles de Europa,2012(25):3-26
[40] SCHOCH L,CLAUSEN J. Women within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Contemporary challenges[M]//CERVIN G, NICOLAS C. Histories of women's work in global sport:A man's world?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299-326
[41] GHADAMI M,HENRY I. Developing culturally specific tools for the evalu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 diverse national contexts: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2015,32(8):986-1000 doi: 10.1080/09523367.2015.1040223
[42] GIRGINOV V.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M]//WINAND M, ANAGNOSTOPOULOS C. Research handbook on sport governance.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9:89-101
[43] CHAPPELET J L,CLAUSEN J,BAYLE 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M]// SHILBURY D, FERKINS L.Routledge handbook of sport governance. London:Routledge,2019:197-212
[44] SCHEU A,PREUß H,KÖNECKE T.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A review[J]. Journal of Global Sport Management,2021,6(3):212-233 doi: 10.1080/24704067.2019.1566757
[45] WOLFE S D,GOGISHVILI D,CHAPPELET J L,et al. The urban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mega-events: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lobal games[J]. Sport in Society,2022,25(10):2079-2087 doi: 10.1080/17430437.2021.1903438
[46] SANTINI D,HENDERSON H. 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race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A ranking of Summer Olympi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progress[J]. Emerald Open Research,2023,1(4):1-24
[47] WATT P. 'It's not for us' regeneration,the 2012 Olympics and the gentrification of East London[J]. City,2013,17(1):99-118 doi: 10.1080/13604813.2012.754190
[48] WEED M,COREN E,FIORE J,et al. The Olympic Games and raising sport particip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evidence and an interrogation of policy for a demonstration effect[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2015,15(2):195-226 doi: 10.1080/16184742.2014.998695
[49] LAWRENCE T B,SUDDABY R.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work[M]//CLEGG S R, LAWRENCE T B,HARDY C.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6:215-254
[50] NITE C,EDWARDS J. From isomorphism to institutional work:Advanc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sport management research[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2021,24(5):815-838 doi: 10.1080/14413523.2021.1896845
[51] 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1):145-179 doi: 10.2307/258610
[52] DOBRY M.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M]. Paris:PFNSP,1986:95-123
[53] GARUD R,HARDY C,MAGUIRE 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s embedded agenc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Organization Studies,2007,28(7):957-969 doi: 10.1177/0170840607078958
[54]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610 doi: 10.2307/258788
[55] DEEPHOUSE D L,BUNDY J,TOST L P,et al.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 Washington DC:Sage 2017:27-54
[56] MÜLLER M,WOLFE S D,GAFFNEY C,et al. An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Olympic Games[J]. Nature Sustainability,2021,4(4):340-348 doi: 10.1038/s41893-021-00696-5
[57] MAGUIRE S,HARDY C. Discourse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The decline of DD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52(1):148-178 doi: 10.5465/amj.2009.36461993
[58] BAYLE E,RAYNER H. Sociology of a scandal:The emergence of 'FIFAgate'[J]. Soccer & Society,2018,19(4):593-611
[59] BERLAND N,PEZET A. Les études critiques en management,une perspective française[M]. Quebec: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val,2009:131-162
[60] DIMAGGIO P J,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doi: 10.2307/2095101
[61] HARDY C,MAGUIRE 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M]//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8:198-217
[62] ZIETSMA C,LAWRENCE T B. Institutional wor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The interplay of boundary work and practice work[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0,55(2):189-221 doi: 10.2189/asqu.2010.55.2.189
[63] ROULET T. Les evaluations eociales en stratégie:Légitimité,réputation,statut,stigmate et cie[M]//SEBASTIEN L. Les grands courants en management stratégique. Caen,EMS(Editions Management et Société),2019:348-423
[64] MOON P,BAYLE E,FRANÇOIS A. Assessing inter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s'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Toward integrat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ir main sports events[J].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2022,3:752085 doi: 10.3389/fspor.2021.752085
[65] BEN SLIMANE K,LECA B. For an approach based on resources and skills of institutional work[J].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4,19(1):85-93
[66] MAUSS M. Essai sur le don: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M]. 4th éd.Paris:PUF,Collection Quadrige,2023:248
[67] VERSCHUUREN P. Whistleblowing determina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porting channel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sector[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2020,23(1):142-154 doi: 10.1016/j.smr.2019.07.002
[68] GRELL 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human rights reforms:Game changer or mere window dressing?[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2018,17:160-169 doi: 10.1007/s40318-018-0127-x
[69] BAYLE E. Changes to the IOC's governance during Thomas Bach's presidency:Intense institutional work to achieve balance and compromise[J/OL].[2024-02-06]. Sport in Society,2024:1-25. https://doi.org/10.1080/17430437.2024.2310696
-
期刊类型引用(4)
1. 向会英. 国际体育法新维度、新视角:AI改革与体育规则演变——第26届世界体育法大会综述. 体育科研. 2025(02): 23-31+4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刘睿,刘建,郑国华. 电竞入奥的历程、现状与展望——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社会学诠释. 体育学研究. 2025(01): 77-8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李晨曦,于思远,刘波. 以奥林匹克价值观和人工智能创新为引领:《奥林匹克AI议程》的全景解读与中国进路.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5(02): 163-17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王菘,曹莉,纪璇,尹莉君. 儒家人文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对话与融通.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11): 18-2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0)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42
- HTML全文浏览量: 21
- PDF下载量: 27
- 被引次数: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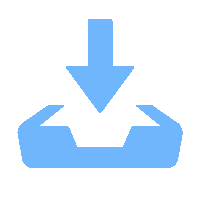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