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Governance Technology to Technology Governance: Forma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Paradox"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
摘要:
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融合。不断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实现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但在转型实践中的“技术悖论”阻碍着数字技术应然效能的发挥。在探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发现,技术失效、权利失衡、治理失真和制度失灵是“技术悖论”的4种具体表现,而技术适配不足、理念转变滞后、制度革新缓慢、主体能力缺位是诱发“技术悖论”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为推动体育治理范式转换、助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坚持场景化治理,科学推动数字技术的“适体化”改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引领数字体育治理理念转变;坚持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稳步促进数字体育治理制度优化;坚持“人治”与“技治”相结合,不断强化数字体育治理主体能力培养。
Abstract: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is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port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to realize its modernization, but the existence of "technology paradox"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hinders th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the four manifestations of the "technological paradox" in practice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failure, power imbalance, governance distortion and institutional failure are explored. And,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adaptation, lagging conceptual change, slow system innovation, and lack of subject ability are the main reasons to induce the paradox.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to adhere to the scenario-based governance to promote its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follow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to accelerate the concept transformation, to obey the multi-subject value co-creation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to combine the "human ruled" and "technology ruled"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digital sport governance subject ability, which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better help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port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governance ability.
-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伴随着社会进步而迅速勃兴的数字技术正对人类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冲击[1]。这种冲击既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创造”,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运行的本原秩序。其中,治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工具,自然也难以回避。如何变革既有治理以有效回应时代流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生活与治理的全面变革;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上述政策深刻体现出数字技术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科技创新,其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更迭,故能在国家治理实践场域中为政府赋能、为社会赋权、为市场提质增效,以形塑和强化国家治理的多元共治格局[2]。
在此背景下,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积极回应这种生产力变革。目前,在实践层面,我国浙江、江苏等少数省市已经广泛开展了数字赋能体育治理的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层面,诸多学者围绕已有的实践探索,对基层(社区)体育治理[3]、体育产业发展和治理[4]、智慧场馆建设[5]、体育发展格局构建[6]等有关领域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现有研究对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和现实效用的讨论偏多,对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所折射出的制度理性和数字技术的价值理性探讨偏少。加之,由于数字技术自身的负面效应及其与治理制度互嵌水平不高等客观因素[7-8],“技术悖论”便成为推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技术—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在厘清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具体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剖析数字时代体育治理的“技术悖论”,并就此提出对应的消解建议,以期为有效推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助力实现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
2.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及“技术悖论”的内涵
2.1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从国家层面看,“数字潮流”已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地融入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理念、规则及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子集之一,体育治理必然需要积极调适以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的变革趋势之中。从体育层面看,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可为改善体育治理提供新的治理技术、手段和模式,实现体育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从而提升体育治理的实际效能[9]。对此,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PEST)分析模型即说明了技术变革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展现出科技革命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所扮演的愈发不可替代的角色。同时,这也意味着科技革命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并深刻影响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10]。所以,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体育治理,数字技术反映出的本质价值不但不会局限于工具层面,而且能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将数字技术“嵌入”体育治理的过程,抑或可理解为一个通过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深度融合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动态过程,最终演化成能够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数字体育治理。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能够通过重塑体育治理流程、优化体育治理机制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治理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实现以数字化推进体育治理的现代化。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链接速率、数据、算法、算力等方面具备明显的性能优势,其更迭周期更短、扩散效率更高、影响范围更广[11],对体育治理的影响也更加深入且全面。整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变化:①利用技术变革体育治理的物理空间,即以数字技术赋能的方式推进传统物理空间的转型升级,实现治理的平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例如,浙江、北京、贵州等省市陆续建立的地方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②利用数字技术赋权的方式拓展体育治理的社会(市场)空间,畅通和拓宽市场、社会及个人协同参与体育治理的渠道,提升不同主体共同参与体育发展和治理的能力。例如,上海推行的公共体育服务配送,通过线上点单、线下配送的方式,切实满足了群众体育健身的实际需求[12]。③推动体育治理的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融合,提升体育治理的敏捷性、精准性。例如,全国各地正大力推行的体育政务服务“掌上办”“指尖办”,对提升体育赛事活动申办审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经营许可等具体业务的处理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2.2 “技术—治理”互动下的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技术创新始终是推动治理范式变革的重要抓手[13]。在早期研究中,技术通常被视为治理的对象,强调人在技术研发、应用等各环节中对其进行规约,旨在突出技术之于治理的工具价值,即“治理技术”(governance technology)范式。随着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范式开始兴起,即通过技术与治理(制度)的深度融合,促使技术成为治理的“准主体”,以此实现治理(制度)的革新与优化,凸显技术治理的制度属性和理性价值,最终呈现出治理的善治逻辑[14]。这种从“治理技术”到“技术治理”的治理范式转型折射出“技术”与“治理”两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和分析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从治理技术视角看,尽管治理技术作为传统的治理模式着重于技术工具论,即主要强调治理技术的工具价值,将技术更多地视为一种方法和手段,并受管理者的支配与使用[15]。但这种治理技术并不特指狭义上的科技手段,而是一种包括体制、机制层面科学设计在内的广义的技术概念,如科学行政管理、项目管理制度、工作绩效评估等。从我国体育治理的演进历程看,我国体育治理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政府统管下的多部门联合治理阶段(1949—1978年);体育部门全权负责的举国体制阶段(1978—1992年);体育职业化背景下体育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阶段(1992—2001年);体育行政部门主导治理、市场和社会初步参与协同治理阶段(2001—2012年);政、社、市等多元主体趋于共同治理阶段(2012年至今)[15]。这种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到社会、市场的逐步介入,再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演进历程,就包含着治理技术于体育管理领域的具体应用。这种演变历程在展现我国体育治理能力渐进式增长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体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与体育治理能力的展现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技术与治理“互动”的结果。然而,技术和体育治理的结合并不总是完美的。以单项体育协会改革为例,协会管理制度作为现代治理技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对调适政、社、市不同主体间的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体育治理而言,以往多认为构建对应的协会管理制度并加以“去行政化”,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体育治理的有序运行。但事实上,单一关注单项体育协会的去行政化和实体化改革,不仅难以真正实现单项体育协会的行政剥离,还可能会进一步引致不同层级政府和协会之间治理关系的脱序[16]。因此,技术的嵌入并不会天然地为体育治理带来效能的提升;相反,需要技术和治理之间进行良好的耦合与互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两者的内在契合,以真正展现出技术治理的应然效用。
从技术治理范式看,技术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的科学运用,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转[17]。自渠敬东等[18]提出“国家—社会”关系向技术治理转型后,技术治理范式因其在治理效率提升方面的独特价值而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现阶段,随着数字革命的深入,技术治理在现代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故有学者[19]称后工业时代是“一个充满技术治理主义的新时代”。虽然作为新兴产物的技术治理并无准确定义,但该命题的提出至少从根本上明确了技术的进步与治理的进步之间具有紧密的正向关联性[20]。这对于理解和认清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数字)技术治理”逻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技术有限性决定了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唯技术论是不现实且不可取的。尽管技术的不断革新与进步是社会的客观存在,但从技术应用到效能提升并不会一蹴而就,仍需要通过其与治理制度之间的互动、耦合、转译以产生相应的作用。因此,除了考虑两者融合的效率和水平外,由数字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应用风险也不容忽视。若不当使用则可能引发“技术悖论”,使得技术效能难以有效转换为治理效能。例如,数据支撑不足、技术支持不够等因素都会造成治理的“失真”[8]。另一方面,在技术治理中,技术失灵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更与人的活动有关。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角度看,轻视乃至忽视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效率变革,都可能使发展与治理陷入停滞,从而导致技术治理落入“自反性悖论”中。同时,作为治理主体的人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习惯、认知、规范等实践惯性,而实践惯性的客观存在容易导致人常常无法与生产力技术同步演化[21]。因此,在有限理性的驱使下,人们总会“持续释放出抗拒改变、安于现状的力” [22],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变革的发生。在体育治理实践中这种问题也较为常见,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人、财等)成本仍相对较高的情况下,部门、单位及个人对于推动体育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实际意愿并不强[23]。
综上所述,尽管数字技术无法涵盖体育治理的全部内容,但是在体育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在具体探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时,不仅要关注体育治理的本体问题,也应从更大范畴上涵盖对“治理术”的治理。简言之,理解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并不能只着眼于技术创新应用的层面,而应着眼于“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的系统性结合[24]。
3.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技术悖论”的表征
作为新时代体育治理的实践创新,虽然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出场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总是完美的,其天然的风险性易导致技术化治理的负外部性,且随着转型进程的加快与程度的加深,“技术悖论”的问题逐步显现,整体呈现出技术失效、权利失衡、治理失真和制度失灵并存的局面。
3.1 技术失效
技术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治理效率的提升[20],弥补传统科层制结构下行政效率的损失。当前,诸如各地投入使用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体育政务“一网通办”平台、公共体育服务线上配送、全民健身“一张图”等数字化改革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体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部分过度追求工具价值的数字化改革却易引致应然逻辑的偏差,使得效率至上的技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体育善治所追求的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换言之,因技术僭越而形成数字治理之“负能”,消解了技术治理所应具备的正当性、合法性,致使数字技术逐步陷入失效之窘境,从而影响体育治理应然效能的发挥。
(1)不当的数字技术应用有损体育发展中的社会公平。立足于技术本身,技术治理效能的释放主要源于数字技术的“(自我)生产—复制—再现”循环,并由此形成复刻现实以预测未来的线性算法治理范式。尽管线性算法运转可以带来工作效率的明显提升,但不当的线性化思维会导致算法“歧视”有违效率最优的边缘群体(如儿童、老年人),使体育治理的均衡性、公平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2)不当的数字技术应用易催生片面的数字形式主义。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工作依然在既有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内展开,并通过科层制中的压力机制进行传导,而后向下转化为基层治理任务。科层制的理性精神强调以有“迹”可寻来体现行政运作的过程与绩效,但技术变量的加入使得现有管理组织体系和制度结构难以有效承载、约束数字技术的运行。加之,科技本身也处于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中,所以,制度路径依赖与技术工具的简单结合就极易引发数字形式主义问题[25]。以体育政务数据公开为例,作为履行政府职能和强化政务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对于促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服务社会实际需求、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体育政务数据还无法全面及时推进[26]。多数地方政府网站常常只保留了一定的体育数据查询端口,所提供的数据类目偏少、“不好用”、实效性较差,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
(3)不当的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管理者的技术“迷信”。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实质上代表着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其所具备的主体智能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实时化等基本特点使得数字治理效能远超以往[27]。在科层制度压力之下,管理者容易产生“技术全能”“技术至上”等片面思维,催生以“技治”代替“人治”的现象,忽略了人之于治理的关键作用。以智慧体育社区建设为例,在当前实践中普遍存在重技术应用而轻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培养的问题,这种对于治理者—人的主体性的忽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造成“线上社区”与“线下社区”发展的“两张皮”[3]。
3.2 权利失衡
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在推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在于其赋权增能效应。通过对体育治理工具、流程、方式和样态的优化,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拓宽不同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实现对市场的赋权和社会的增能,进而不断调和、重塑体育治理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确保在复杂治理情境下能够建立起具有多元主体协同特点的整体治理模式。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先天禀赋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技术对不同主体赋权增能的非均衡,并由此衍生出权力与权利冲突的问题。权力和权利是现代社会运行最依赖的一对关系,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权利的保障需要权力的行使,而缺乏公正的权力行使,权利的正当性无从谈起;同时,权力的滥用也会影响正当权利的行使,所以权力的行使要有效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28]。
由传统行政权力延伸而来的数字权力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则,只是这种冲突的形式在数字作用下发生了变化,即“技术赋能与技术索权”。一方面,体育治理的成效直接关乎人民体育参与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不同群体数字体育设备的使用能力和数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多重因素,社会弱势群体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例如,线上运动会、云健身等体育新模式的受众群体就相对固定、偏窄,一旦用户不懂操作也就意味着无法正常参加,其基本的体育参与权益亦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技术创新在为体育治理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侵害部分人民群众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29]。另一方面,泛在的数字化发展使得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30]。通过无处不在的数字移动设备,人与人的任何活动信息可以被精准识别并以高度颗粒化的信息流方式被收集、传输进而加以应用。在此基础上,一旦行政主体对数据、算法形成了不当依赖或是对权力产生迷恋,就会引致盲目扩大数字技术应用范围的现象,造成数字公权的扩张,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和自由[31]。更为关键的是,当体育治理问题的特殊性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产生杂糅时,数据权利失衡问题也可能被进一步复杂化。以反兴奋剂治理为例,随着世界反兴奋剂治理工作迈入“数字时代”,运动员生物护照、运动员行踪信息申报等数字化机制已逐步成为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实施手段。在理论上,建立在运动员数据的充分供给与处理基础之上的反兴奋剂治理不能以牺牲运动员的数据权益为代价[32];而实际上,数据主体(运动员)与数据控制者(体育管理机构、体育俱乐部等)之间存在天然的实力差距,导致数据权利义务关系失衡[33],从而引发运动员个人数据的过度处理、信息泄露、权利行使困难等现实问题。显然,这种新兴的、隐性的体育权利失衡问题是在实现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3.3 治理失真
作为数字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代表之一,数据及其应用是驱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在数字体育治理体系中,数字技术将治理要素转化为数据节点,并依靠以节点为中心产生的数据流虚拟还原治理场景(或治理情境),再通过预设算法表达和复现体育问题,形成清晰的虚拟镜像且可以在技术路径上进行加工,从而提升治理效能[34]。这种治理需要大样本数据以管窥全貌而非小样本的个案抽查,即“数据+算力”是数字化治理的“底座”。在理论上,数据的总量越大、算力越强,其所能复现的体育发展问题就越清晰,治理效能也就越高,但与之伴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过于线性的数字逻辑会简化体育治理情境。任何治理场景本质上都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结合体,既是经验事实也是客观事实,而事实之间的连结机理并非机器学习所遵从的线性逻辑,且体育行业特殊性的存在使得一般的治理规则难以完全适用[35]。倘若数字技术只能遵从一般的治理规则,将显性的、可捕捉的体育问题以数据形式展现出来,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例如,在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仅依靠“数据+算法”就有可能产生全民健身决策简单化的风险,使传统复杂的全民健身供求分析演变为单纯的数据分析和技术决策[36]。另一方面,数据的质量高低也会直接决定数字体育治理的实效。具言之:①依托大样本数据分析展开的数字体育治理,对数据来源全面性要求较高。数据越多、覆盖范围越广,其所能映射的问题事实越准确。但我国目前仍有3.33亿的非网民人口,其中还涵盖大量的农村人口、老龄人口等数字弱势群体[37]。倘若无法对其实施数据采集,就难以准确客观地展现我国体育发展的本原面貌。②受限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不均衡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等客观因素,数据对体育治理的支撑作用仍相对有限[38]。因此,一旦数据的有效性、时效性和真实性欠佳或数据总量不足,就容易造成体育治理失真。
3.4 制度失灵
数字技术自身并不具备建构制度的能力,只有将其与对应的标准、规则、架构、流程等制度要素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以达成数字治理的应然效用。事实上,无论是社会的整体变迁,还是某一特定制度的单项改革,总是相对滞后的。这种现象并非现代社会独有,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39]便已提出“文化堕距”(也叫“文化滞后”)的概念,即“社会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许多时候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但与物质条件相适应的文化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随后,有学者[40]借用此理论分析了技术与社会的控制关系,认为技术总是跑在社会发展前头,而习惯、思想、社会安排等都落在后面。
体育治理亦然。在数字技术嵌入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技术治理既是原本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科层制组织刚性权力结构和组织壁垒的约束。以构建体育数据专职管理机构为例,我国《数据安全法》第6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及数据安全负责”,即“谁管业务、谁管数据,谁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依据此规定,体育领域的数据管理职责就应由体育行政部门承担。但是目前,全国体育系统的数字化管理工作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负责,尚未设置单独的体育数据管理机构,地方层面仅有少数体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38],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制度变革的滞后性。除行政制度外,体育行业自治制度在“数字浪潮”中也面临着一定的失灵。以国际反兴奋剂制度为例,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由于各国反兴奋剂机构所适用的(本国)法律规范差异较大,难以为反兴奋剂活动参与者提供恰当的实施依据及必要的权利保护[41],行业自治制度的调整成为必然,因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针对反兴奋剂数据处理问题制定了《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ISPPPI),以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个人数据权利。尽管以ISPPPI为代表的体育行业自治制度具有保障反兴奋剂公共利益这一合理性基础,但在具体实践中其又会与有关国家的数据立法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实质合法性的不足[42]。并且,相关国家在向WADA传输运动员数据信息时,也可能出现一些隐性的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问题。如此,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制度的脱节,不仅无法提升发展效能,反而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所以,如何在法律规范(硬法)和行业规则(软法)互动框架下更好地回应体育数据治理需要并调和国家、体育组织以及运动员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失衡问题,可能也是未来体育自治在自我完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4.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技术悖论”的成因
通过对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及表征的分析,可以发现治理理念、技术及制度这3个要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决定体育治理范式(从治理技术到技术治理)演化成效高低的关键因素。在结合既有研究与技术治理本质的基础上,从“技术—理念—制度—主体(人)”框架着手,对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技术悖论”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4.1 数字体育治理技术适配不足
技术治理是指在社会运行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治理的活动[43]。如果数字技术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当它被应用于体育治理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从体育治理客体角度看,体育问题特殊性的存在决定了技术嵌入体育治理需要进行对应调适,以追求技术与体育治理机制的协同耦合,而非机械式地“照搬”。一个相对典型的正面案例就是“亚运钉”,其是阿里集团联合杭州亚组委专门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打造的大型体育赛事一体化智能办赛平台。“亚运钉”一方面实现了10万办赛人员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在线、沟通在线、业务在线”大协同,另一方面也涵盖了包括行政审批服务、会议服务、培训服务、赞助商服务、气象服务、医疗服务等不同赛事业务领域的293个应用[44]。这在整体上实现了体育赛事治理中“人”的协同统筹与“事”的高效运转,为保障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这种基于体育特殊性而实施的数字技术综合应用是以往普通协同办公软件所无法实现的。
从数字技术本体角度看,技术创新对于体育发展的“牵引”和“倒逼”作用仍然不充分、不明显,数字体育治理的区域性差异、领域性差异等问题较为显著,具体呈现为:①受限于体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与数字经济的区域差异,数字技术对体育治理转型的“牵引力”呈现出区域间、城乡间的水平不一。以智慧体育社区为例,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像“社区运动家”(嘉兴)、“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海)等相对成熟的智慧体育社区建设样板案例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滞后。②因数字技术在不同体育领域应用程度的不均与数字体育治理场景开发不足等问题,技术创新“倒逼”体育治理转型的作用不明显。现阶段,除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健身休闲、体育新闻、赛事直播等细分领域与数字技术结合相对紧密外,学校体育等其他领域的数字体育治理场景开发缓慢、技术应用的局限性较强。例如,在全民健身治理中,数字技术更多地被用于运动场地及设施设备的改造,而未能真正实现社区体育的整体升级,技术应用相对局限、实际的数字化效果单一[45]。
4.2 数字体育治理理念转变滞后
治理理念转变滞后是导致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技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实践中,作为实施体育治理行为的主体,人对数字技术、数字体育治理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在治理活动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从而影响治理效能的展现。目前,主要存在“技术全能论”和“技术无用论”2种偏颇的理念认知。
“技术全能论”在本质上是对数字技术治理效能的迷信或者说是过度信任,主要表现为“重技术而轻问题”“重最终结果而轻实际过程”等[46]。尽管数字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掌握了更为高效的社会生产力工具,并且可以此为依托来解决之前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技术的功能总是相对有限的,不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技术。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技术的本体意义在于其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存在[47]。因此,混淆或割裂数字技术与体育发展、与人之间的实质关系,而片面地期待以技术的进步完全解决现存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当前在体育治理实践中此类问题已有所显现。从全民健身治理看,尽管全民健身是当前我国体育治理中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一个领域,但数字技术嵌入治理的实际效果仍有待提升。究其缘由,还与数字技术应用相对有限、治理体系融合不够等因素有关[48]。这也深刻反映出数字体育技术治理范式的应然和实然之间差距较大,即技术本身可能是有效的,但只通过技术和体育治理的片面结合不一定能够奏效。
“技术无用论”则是一种对技术应用持保守态度的思想理念,即对新技术持轻视、谨慎或排斥的态度,这是因为其仅关注到技术本身的缺点而未正视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49],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不强、意愿不足。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受限于成本高、压力大以及数字技术单一等各种因素,转型的实际进程相对缓慢,无形中催生出管理者隐性的“技术无用论”思想。例如,有学者[50]在对体育场馆的智能化升级问题进行调研时发现,不少管理者对场馆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认识不足且呈现出一定的“漠视”态度,多认为“在线预订场地、网络购买门票、场馆Wi-Fi覆盖、自动检票等技术应用”即为智能化升级,“财政拨款就可以实现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可见,管理者自身对于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相融合的认知也是不深刻、不全面的。
4.3 数字体育治理制度革新缓慢
相较于技术更新迭代的快速,体育治理制度体系的变革则相对缓慢。一方面,这体现为数字技术与科层制体育治理体系的融合不紧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两张皮”问题。在传统体育治理范式中,受条块分割的制度结构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数字技术应用相对独立、分散,这不仅造成了技术与制度关系的割裂,且衍生出新的叠加于“行政壁垒”之上的“信息孤岛”,加剧了体育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难度,例如,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等既有的体育数据平台之间尚未实现互通互联[51]。同时,扁平化的平台治理结构在理论上能够有效容纳更多的治理主体,实现对市场、社会及个体的赋权增能,从而提升体育公共事务的决策水平和实际供给质量。但在工具性主导下,数字技术本身所遵循的简化逻辑并不能很好地适配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导致单一的治理技术与多元化的治理场景之间产生矛盾,进而体现为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客观事实的全面性之间的冲突[52],使数字体育技术治理走向形式化。
另一方面,体育治理制度也要调适并呼应数字技术的变革。社会变迁的客观性决定了并不会存在一成不变的管理制度,因此,在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出现的同时,社会制度也必然需要对应调适,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制度变迁总是需要动力的,数字技术又是否能从根本上驱动我国体育治理结构体系的变革?对此,从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视角或许能够有所发现。目前,尽管通过对科层制度内外部主体的协作、交流提供便利等方式,数字技术有效提升了政府体育治理的效率[21],但这种有限的收益可能还未达到成为制度变革主要动力的程度。以公共体育数据开放为例,公共体育数据的流通、共享与应用对数据资源价值的发挥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数据安全标准规范的模糊、体育行政部门内部监督机制的不明等现实原因,公共体育数据的开放始终难以全面推进,体育数据的应然价值无法充分释放[26]。
4.4 数字体育治理主体能力缺位
从数字技术应用到产生相应的数字体育治理能力,其间的作用因素并不局限于“技术”,在更大程度上还与人的认知有关,即“是否用技术”的问题。在缺乏科学认知的前提下,人与技术相结合的能力、凭借技术识别体育问题的能力等数字素养就无法养成,继而造成人掌握和应用技术的能力有所欠缺。
从体育治理的主导者角度看:一方面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人员较少而事务繁多,使得体制内人员不具备主动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的时间、精力等客观条件,内在动力不足[53];另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内开展的数字培训项目依旧为传统的计算机技术或电子政务的应用能力培训,内容相对浅显、陈旧,无法有效满足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54],外在拉力不足。由此造成体育管理者不具备良好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客观事实。
从体育治理的协同参与者角度看,除市场主体情况相对理想外,包括个人、体育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其他体育治理参与者的数字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农村人口等都是“数字边缘”弱势人群,其并不具备感知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素养较差。加之,目前我国体育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弱势人群拥有的参与数字体育治理的物质条件较为有限。在推动体育治理向技术治理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就难以切实保障每个公民应有的体育权益,也就无法落实体育发展为人民的价值理念。
5.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技术悖论”的消解
5.1 坚持场景化治理,科学推动数字技术的“适体化”改造
技术治理是一个实现场景化的动态过程[52]。场景化治理强调对问题本身的把握,以及对各种治理手段和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灵活运用。之所以要强调数字体育治理的场景化:一是因为技术本身的有限性不足以适配体育问题的多样性;二是因为体育本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场景集合体,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全方位体育交流互动,小至不同类型(运动项目)赛事活动中人与人的联系,两者共同赋予了数字体育治理场景化的合理性基础。基于此,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就需要注重对治理场景的开发,通过场景构建引领技术适配,进而助推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一方面,应不断强化数字体育治理场景需求的有效性。对技术治理而言,有效需求就是要将数字技术与体育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技术应用的适切性。在实践中,在全面梳理体育业务需求的基础上,可结合不同细分体育领域的工作特点开展专项调研,逐步挖掘对应领域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难点,并通过制定场景应用清单等方式不断细化转型目标、明确建设责任。具体可参考浙江省印发的《数字体育建设“十四五”规划》和《2023年体育数字化改革工作要点和重点项目建设总体方案》等,以整体勾勒出央地两级数字体育治理的“四梁八柱”,确保“干有方向”“做有抓手”。
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数字体育治理场景构建的系统性。切实依托数字体育治理场景的技术特性,不断推动场景建设由分散向系统、由碎片向整体转变。尝试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全面整合传统的碎片化体育治理,打破因场景碎片、行政壁垒等客观因素而诱发的“数据孤岛”问题。例如,将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等业务领域的治理工作纳入数字政府的整体建设,实现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协同办公一体化。与此同时,也要积极鼓励不同部门、领域、主体围绕体育赛事、体育产业等其他业务领域共同进行场景开发,推动“多跨场景”协同机制的建立,以防范现代体育发展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5.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引领数字体育治理理念的转变
技术治理范式中的技术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类发展目标的工具[55]。尽管数字技术这一新型社会生产力的出现已经极大地“虚化”了人及人活动的社会场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即目的与手段。所以,数字技术仍应回归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逻辑,以避免数字技术的价值异化与失范。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的客观理性相结合,实现数字体育治理之共建。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我国体育发展的价值追寻,也是体育治理的逻辑所在。因此,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就应将人民性理念贯穿于治理的始终,明确人的主导地位与技术的辅助地位,不断厚植“人技共治”的价值内核,以价值引领技术应用理念的成熟化。同时,在深刻把握人与科技本质关系的基础上,也应进一步明确技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群众体育参与的促进价值,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更好地识别和分析群众的体育需求,变“人机交互”为“人际交互”,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发展和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国家体育治理的现代化汲取更广泛的人民力量。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将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实现数字体育治理之共治。尽管过程和结果是2种不同的方向性问题,但两者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线性技术治理逻辑主导下,引入过程导向有利于纠偏过度的结果导向,因为治理过程更强调任务的每个阶段都是有序、可控的,且需要不断地评估和优化,所以不会局限于治理结果本身,而要强调数字体育治理的过程管理。一方面要优化治理过程的结构。通过数字技术不断拓展治理行为边界、疏通治理参与渠道、营造良好的多元治理参与氛围,广泛吸纳各类体育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实施,推动多元主体的协同整合与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要关注治理过程的水平。以技术应用提高体育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等数字能力建设,将数字优势充分转化为体育治理水平提升的动能。例如,针对体育数据的全生命管理周期进行规则调适,一旦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出现数据风险,可以做到及时响应、快速处理,避免因技术失效(失灵)带来更大程度的损失。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体育治理要将温度和效度相结合,实现数字体育治理成果之共享。尽管数字技术为体育治理带来了效度(如效率、精度、清晰度等)的提升,但也可能引发治理温度(如柔性、伦理性、人本性等)的降低。因此,要从根本上彰显人的主体性,不断推动数字体育治理由高级化向基础化转变,实现科技善治,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的体育治理参与中对技术应用可感、可知、可及。例如:扩大体育政务业务“掌上办”“指尖办”的覆盖范围;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丰富公共体育数据、体育政务数据公开的数字化渠道,助推体育行政治理提质增效;积极推动数字体育治理方式和手段的适老化、适残化改造与升级,确保特殊人群也能无差别共享数字体育发展成果,真正将“数字红利”“数字智慧”转化为体育治理之实效。
5.3 坚持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稳步促进数字体育治理制度的优化
技术赋能难以脱离制度的保障,制度创新也无法缺少技术作用的加持,所以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依旧需要紧密依托体育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浪潮”裹挟下,技术治理所展现出的情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远超传统体育治理范式的管辖范畴,既可能包含国际和国内,也可能涵盖虚拟和现实。因此,尽管受现代善治理念影响的体育治理已经转向合作生产,以应对体育现代化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但合作生产在面对复杂情境和多元价值诉求等方面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故需要再次推动体育治理由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这是由社会现代性和数字化转型共同决定的。
(1)凝聚数字体育治理的价值共识,为实现价值共创塑造情境。价值共识是不同主体对治理目标、手段、资源等方面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认同,抑或可理解为一种治理文化,是人的主体性体现。在推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欲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效能,仅关注技术和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价值共识(文化)才是支撑数字体育治理有序运转的关键。所以,要切实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根基,打造面向生活的体育文化,充分发挥价值共识对体育改革和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引领、支撑作用,以适应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治理新逻辑[56]。
(2)重塑数字体育治理的生产空间,为价值共创提供交流载体。不同体育治理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往往需要一定的平台或载体。在传统体育治理范式中,主要依靠体育社会组织、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等制度性机制进行跨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其在信息整合、信息传递、供给配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数字技术的嵌入能够为体育治理生产空间的重塑提供有力支持。①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平台等数字技术,深化拓展空间功能,加强体育治理的文化、交互、激励等属性;②依托体育数据平台、体育政务平台等虚拟空间的建设与互通,深化拓展空间形式,以沉浸式、交互性、场景化方式创新体育治理场景,促进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客观事实的全面性深度融合;③凭借数字技术的“下沉”与“渗透”,进一步优化空间内容,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体育治理变革,紧密捏合“治理需求—治理技术—治理供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治理有效性,具体可以参考当前部分省市地方全民健身治理中的“线上点单、线下配送”。
(3)推动数字体育治理组织再造,为实现价值共创提供基础支撑。组织再造的本质是基于当前社会稳定运行而对治理组织进行的适应性改造,以重建社会的结构和秩序。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体育治理应当及时从行政治理与行业自治2个层面协同推进组织再造。①在行政治理层面,依据数字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快推动体育行政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自上而下地对各省市地方体育政务的“上云赋智”和体育公共数据开放等事项予以统筹,可通过局部试点、整体推广的方式,稳步有序地推进全国范围内的体育行政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数据驱动范式,紧密结合各地需求,构筑起央地协同的数字业务平台,主动对接其他部门、领域、主体,以形成集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于一体的多跨协同机制体系,提升全国体育行政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②在行业自治层面,可以尝试推动体育社会组织自身架构、核心业务、行业规范等方面的数智化改革,以重点突破驱动行业自治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如中国篮球协会基于国内海量篮球数据信息所建立的“K8平台”可对人才选拔、赛事优化等行业自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针对体育数据治理等关键领域,也应尽快依据国家相关立法,加快完善体育数据的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以有效防范体育数据的安全风险及“长臂管辖”等治理新问题。
5.4 坚持“人治”与“技治”相结合,不断强化数字体育治理主体能力的培养
简·芳汀[57]认为,信息技术是“被执行的技术”,故其应用结果会受到组织文化、结构、成员认知以及政治嵌入的影响。换言之,数字技术对体育治理效能的提升就像科技发展中的摩尔定律一样,是有上限的。数字技术并不会成为解决体育发展问题的“万能公式”,这就需要将有限的“技治”和(在某种程度上)无限的“人治”相融合,从而真正发挥技术治理的作用。
从数字技术看:一方面要立足技术有限性,合理限缩技术应用范围。缩小数字体育治理的范围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技术的嵌入,而是在技术理性的引领下审慎转型。①以技术的成熟度为基准,“成熟一个、推广一个”,稳步推进体育治理转型,对同一技术在不同体育治理情境中的技术有效性进行充分的验证,不盲目推广技术应用,避免由技术不确定性引致技术风险。②以“小设计”为主、“大设计”为辅,通过局部改造与渐进式改革,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道路,降低转型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坚持“软硬”结合,以补足技术治理之缺陷。在实践中,为防止技术的“一刀切”,需要通过软治理技术弥补硬技术治理的“空白”,充分彰显人文关怀。例如:①通过发挥公共政策工具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推动我国数字体育区域间、行业间的均衡化发展;②建立数字技术应用的协商机制、评估机制,定期收集包括民众在内的不同体育治理主体的使用反馈意见,为数字终端应用的动态调适和精准创新提供实际依据;③建立健全数字体育治理评价考核体系,不完全以数据和形式上的“有无”来判断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科学结合群众参与度、满意度和体验感等主观性指标来综合评价体育治理转型的程度和水平[58]。
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应强化人的数字素养培养,提升人对技术的掌控力,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体育治理,凸显人的自主性。①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组织在体育数字治理变革中的领导作用,厘清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权限和行为边界,为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培育和数字能力提升明确方向。②依据实际需要,结合国家《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关于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治理能力的相关要求,不断改革体育管理体制内的数字技术培训体系,建立囊括专项培训、考核测评、动态监控等内容的分层分类培训机制。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数据信息获取、数字内容创建、数字信息交互、数字安全维护、数字伦理和法治保障等重点领域,适时更新数字技术应用培训内容,定期邀请行业领域内的专家讲课与培训,主动对接数字技术发展前沿动态,不断提升体育管理人员的数字洞察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和数字引领力,加强“人数协同”。③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协同的数字体育合作发展模式。依托既有的体育平台资源,如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民健身示范点、智能体育综合体等,广泛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为大众提供学习机会,助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整体提升。
6. 结束语
积极回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然而,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的融合并不能只局限于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层面,更应深刻观照体育体制变革层面的价值理性,故从治理技术到技术治理的范式转换就成为历史必然。然而,变革并不会总是指向正确的方向,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初步显现的“技术悖论”预示着只有坚持开放、审慎变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体育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贡献声明:蒋亚斌: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作者贡献声明:张伟国:收集论文资料,修改、校对论文。 -
[1] 马长山. 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及其法治化展开[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38(5):3-16 [2] 黄建伟,陈玲玲.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J]. 理论与改革,2019(1):86-95 [3] 胡婕婷,王新建,杨建设,等. 数字赋能与治理革新:智慧体育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实践策略与优化路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2):50-56 doi: 10.3969/j.issn.1000-520X.2022.02.007 [4] 许坚,周勇. 技术赋能体育市场监管体系现代化:逻辑、困境与纾解[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41(4):125-130 doi: 10.12163/j.ssu.20220336 [5] 傅钢强,魏歆媚,刘东锋. 人工智能赋能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的基本表征、应用价值及深化路径[J]. 体育学研究,2021,35(4):20-28 [6] 吴彰忠,钟亚平. 数字赋能构建体育发展新格局:理论逻辑与实践基础[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5):553-558 [7] 张铤. 技术治理何以失灵?[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38(11):77-81 [8] 梁玉成,政光景. 打破技术治理悖论:从“默顿系统” 迈向“牛顿系统” 的技术治理转型[J]. 社会发展研究,2020,7(1):4-22 [9] 董传升,张立. 新时代泛在体育治理的逻辑与策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6):1-11 [10] 孟天广.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机制与路径:兼论“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向驱动[J]. 治理研究,2021,37(1):5-14 doi: 10.3969/j.issn.1007-9092.2021.01.002 [11] 周念利,吴希贤. 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理论逻辑与典型事实[J]. 当代亚太,2021(6):78-101 [12] 上海市体育局. 2023年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召开[EB/OL]. [2023-08-15]. http://tyj.sh.gov.cn/gzdt2/20230208/d2b948e7d87141ca9f723f8bd11e5cdf.html [13] 辛勇飞. 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S1):26-31 [14] 宋辰熙,刘铮. 从“治理技术” 到“技术治理”:社会治理的范式转换与路径选择[J]. 宁夏社会科学,2019(6):125-130 [15] 董红刚.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9):18-24 doi: 10.3969/j.issn.1000-520X.2018.09.003 [16] 张兵. 地方足球协会运行机理及改革策略[J]. 体育科学,2017,37(11):91-97 [17] 刘永谋. 伪技术治理:类型、逻辑与应对[J]. 探索与争鸣,2022(11):132-139 doi: 10.3969/j.issn.1004-2229.2022.11.020 [18]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9] 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M]. London: Routledge, 1999: 2-3
[20] 彭亚平. 治理和技术如何结合?:技术治理的思想根源与研究进路[J]. 社会主义研究,2019(4):71-78 [21] 刘翠霞. 迈向“负责任地创新治理”:当代社会技术治理的失灵症候与疗治可能[J]. 社会科学,2021(10):87-95 [22] 余伟如. 资本的惯性运转及其批判:马克思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的当代解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42(6):22-29 [23] 孟云鹏. 我国城市体育智能治理系统构建与改革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9):12-28 [24] 郭余豪,石宏伟. 基层政府推进数字治理的价值逻辑、现实障碍与破解对策[J]. 领导科学,2023(3):89-94 doi: 10.3969/j.issn.1003-2606.2023.03.019 [25] 孙会岩,王玉莹.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J]. 电子政务,2023(2):107-114 [26] 蒋亚斌,张恩利,任波,等. 我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法治困境及其应对:以体育数据要素为视角的分析[J]. 体育科学,2022,42(6):3-10 [27] 董石桃,董秀芳.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2(6):66-73 [28] 容志.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J]. 人民论坛,2023(3):60-63 doi: 10.3969/j.issn.1004-3381.2023.03.013 [29] 杨嵘均. “技术索权” 视角下信息弱势体公共服务供给的偏狭性及其治理[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6):123-130 [30] 马长山. 数字公民的身份确认及权利保障[J]. 法学研究,2023,45(4):21-39 [31] 陈水生,谢仪. 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及其复归:基于“数字抗疫” 的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2023(2):18-30 [32] 徐伟康,田思源. 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3):276-281 [33] 刘韵. 权利义务关系视角下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及其基本原则: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分析[J]. 体育科学,2021,41(1):21-28 [34] 向玉琼. 数字治理等同于清晰治理吗?:审视数字治理中的清晰与模糊[J]. 天津社会科学,2023,14(3):51-58 [35] 韩勇. 体育特殊性、问题导向与中国实践:体育法学的研究进路[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55-68 [36] 郇昌店,郑贺.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价值、障碍与对策[J]. 体育文化导刊,2022(11):42-48 doi: 10.3969/j.issn.1671-1572.2022.11.008 [3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8-28].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38] 李若洋,钟亚平. 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J]. 体育科学,2022,42(5):18-28 [39] 奥格本. 社会变迁: 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 王晓毅, 陈育国,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133 [40] VOLTI R. Societ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M].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14: 349-351
[41] 裘韵.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审思[J]. 体育科研,2020,41(2):45-53 doi: 10.12064/ssr.20200205 [42] 李睿智. 反兴奋剂个人信息处理国际行业规则完善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21: 121 [43] 刘永谋. 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J]. 哲学动态,2021(1):43-45 [44] 吴蕾, 肖宇轩. 杭州亚运 云上转播[N]. 深圳商报, 2023-09-22(A03) [45] 冯俣睿,郑家鲲. 数字技术助推社区体育精细化治理:内涵、机制和路径[J]. 体育学研究,2023,37(2):85-95 [46] 张康之. 时代特征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J]. 学术界,2007(1):49-58 [47] 李日容.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与化解技术危险的可能出路[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39(3):74-81 [48] 张文静,沈克印. 数字赋能:体育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施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7):13-21 doi: 10.3969/j.issn.1000-520X.2022.07.002 [49] 范炜烽,白云腾. 何以破解“数字悬浮”:基层数字治理的执行异化问题分析[J]. 电子政务,2023(10):59-70 [50] 高进,武连全,柴王军,等.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J]. 体育学研究,2022,36(5):63-73 [51] 张晓强,罗小兵,鲁长芬,等. 我国体育数字治理理论阐释、风险挑战与效能释放[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3,42(5):55-61 [52] 吕德文. 治理技术如何适配国家机器: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及其限度[J]. 探索与争鸣,2019(6):59-67 [53] 侯雪婷,段明会,蒋亚斌. 组织变革理论视域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3,39(4):29-37 [54] 蒋敏娟,翟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挑战与应对方略[J]. 电子政务,2022(1):54-65 [55] 颜昌武,杨郑媛. 什么是技术治理?[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2):11-22 [56] 任海. 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J]. 体育科学,2020,40(7):3-13 [57] 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 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 邵国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79-86 [58] 蒋亚斌,张恩利,王孟,等.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中我国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机理、难点与突破[J]. 体育科学,2023,43(11):40-50 -
期刊类型引用(6)
1. 宋昊洋. 数字体育的发展策略及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农村科学实验. 2025(01): 48-5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刘运富,刘星.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理论源流、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 湖北体育科技. 2025(02): 92-9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宋亨国,王淋燕. 场景、关系:体育形成数据及其权利形态的生成. 体育与科学. 2025(02): 41-5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国翠翠,藏威,李国金,王书芳,杨宇豪,魏子仪. 河北省虚拟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当代体育科技. 2025(11): 87-8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5. 邹新娴,段细艳,布特.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全民健身发展效率及其空间特征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5(04): 1-1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6. 霍鹏宇,史曙生,李冲,方萍,朱厚伟. 数智赋能青少年体质健康协同治理:内涵、价值与路径. 体育文化导刊. 2025(04): 1-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0)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77
- HTML全文浏览量: 33
- PDF下载量: 25
- 被引次数: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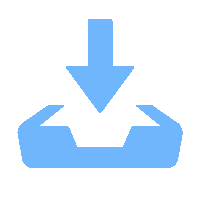 下载:
下载: